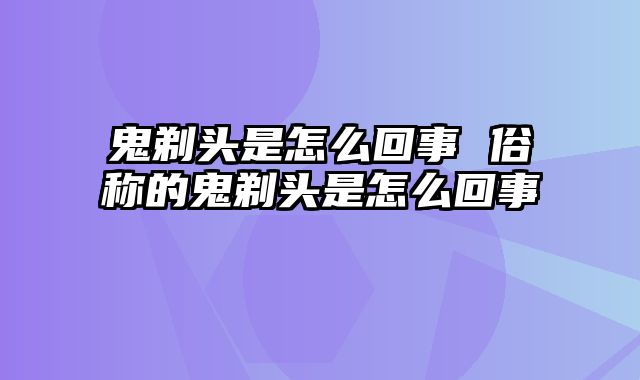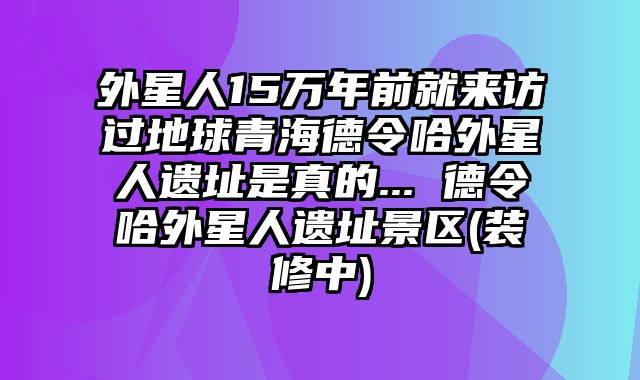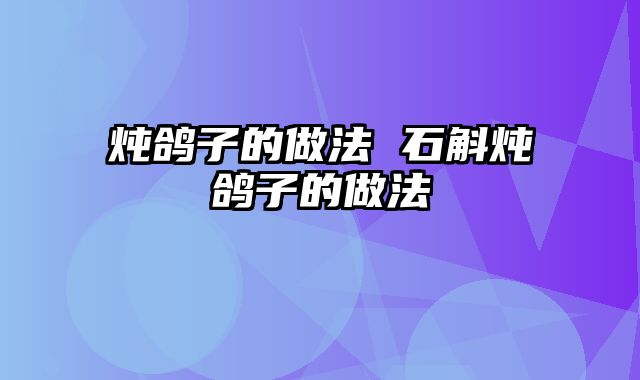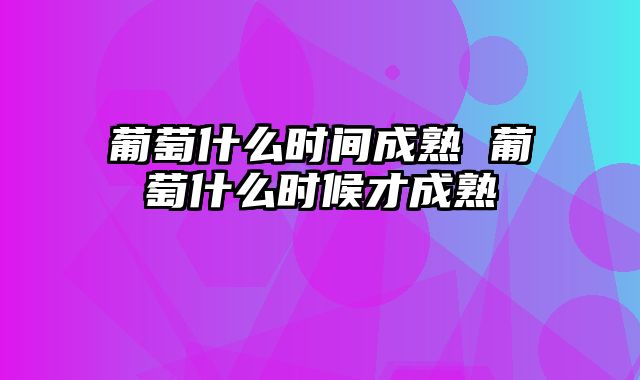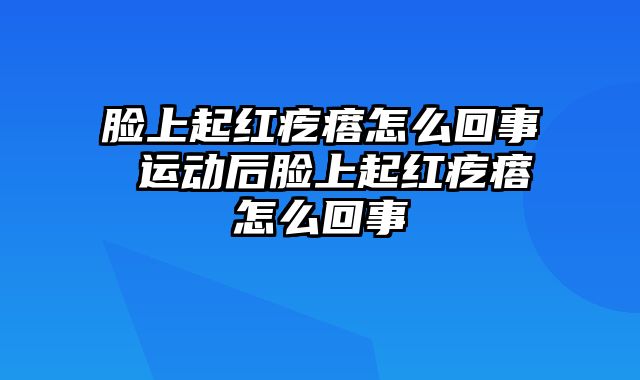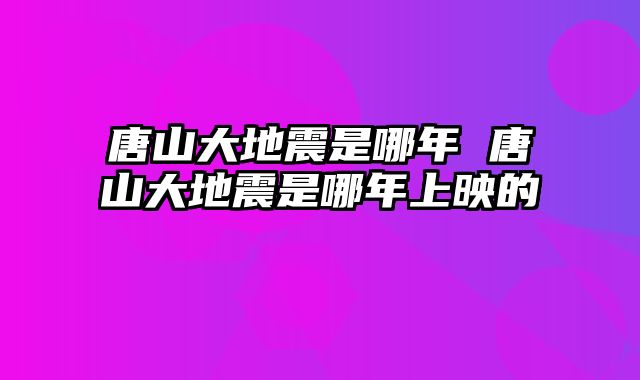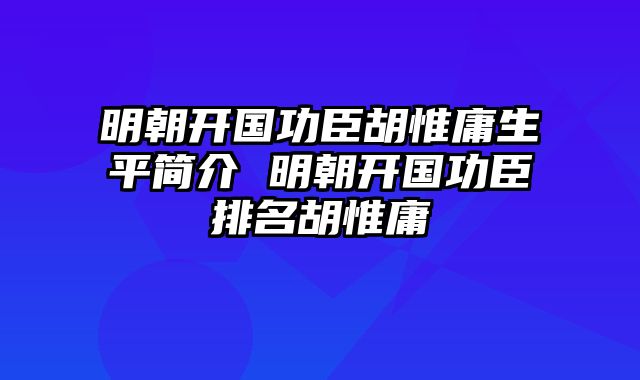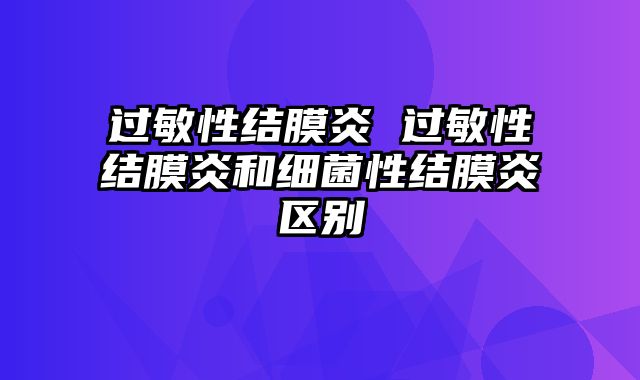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东晋王朝如同一抹斜阳余晖,在风雨飘摇中缓缓沉落。而晋恭帝司马德文,正是这抹余晖中最后的一缕光影。作为东晋的末代皇帝,他的命运不仅承载着一个王朝的终结,也映射出乱世中皇权的脆弱与无奈。他并非昏庸之主,却生不逢时;他心怀复国之志,却无力回天。在刘裕步步紧逼的政治风暴中,司马德文最终成为权力更迭的牺牲品,以悲剧收场。

司马德文,字德文,是晋孝武帝司马曜之子,晋安帝司马德宗之弟。他出生于公元386年,正值东晋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彼时北方五胡乱华,中原沦陷,晋室南渡已逾六十年,朝廷内部权臣当道,外部强敌环伺。其兄晋安帝即位后,因智力低下,无法理政,朝政大权长期落入桓玄、刘裕等权臣之手。司马德文早年便以忠诚勤勉著称,常代兄处理政务,实际上承担了部分皇帝职责。
公元419年,权臣刘裕为篡位铺路,先弑晋安帝,随后拥立司马德文为帝,改元“元熙”。然而,这场“登基”实为政治傀儡的开端。刘裕早已掌控军政大权,司马德文虽居帝位,却无实权,形同囚徒。他在位仅一年有余,所有诏令皆出自刘裕之手,宫廷内外皆由刘裕亲信把守。史载司马德文每日焚香礼佛,祈求国祚延续,然大势已去,无可挽回。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德文并非被动接受命运。据《晋书》记载,他曾秘密联络忠于晋室的旧臣,试图组织抵抗,但因力量悬殊,计划未果。更有传说称,他曾在宫中藏匿兵甲,准备伺机起事,却被刘裕耳目察觉,最终未能成行。这些细节虽不见于正史详载,但在后世史家笔下常被引为悲壮之举,彰显其不甘亡国之心。
公元420年六月,刘裕逼迫司马德文禅位于己,建立刘宋,东晋正式灭亡。禅让仪式上,司马德文亲自捧玺绶交予刘裕,面无愠色,唯叹息曰:“桓灵之世,汉祚已衰;今我晋室,亦复如是。”言语中满是无奈与苍凉。退位后,他被封为零陵王,迁居秣陵,形同软禁。尽管刘宋初年表面优待前朝皇室,实则严密监控,不容其有任何政治活动。
更令人唏嘘的是,司马德文的结局极为惨烈。据《资治通鉴》记载,刘裕恐其日后成为反叛象征,遂于公元421年派兵入府,逼其自尽。司马德文信奉佛教,拒绝自杀,言:“佛教戒杀生,我岂可自戕?”士兵遂以棉被蒙面将其闷死,年仅三十六岁。这一幕成为中国历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瞬间——不仅是东晋的终结,更是门阀政治向寒门崛起过渡的血腥注脚。
司马德文的一生,是理想与现实激烈碰撞的缩影。他具备帝王应有的德行与操守,却缺乏扭转乾坤的实力与时机。他的悲剧,不只是个人命运的不幸,更是整个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写照。东晋百余年,皇权长期受制于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世家大族,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格局。而刘裕出身寒门,凭借军功上位,最终取而代之,标志着贵族政治时代的结束和寒门武将掌权的新纪元。
从历史角度看,司马德文的存在提醒我们:王朝的兴替往往不取决于君主个人品德,而在于制度、军事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迁。东晋末年,流民武装崛起,中央财政崩溃,地方割据严重,皇权早已名存实亡。即便司马德文再贤明,也难以逆转这一趋势。他的退场,更像是历史必然中的个体回响。
后世对司马德文的评价多持同情态度。唐代房玄龄在《晋书》中评曰:“恭帝恭俭有德,而运属陵迟,虽欲振起,势不可为。”宋代司马光亦感叹:“使晋有雄才,或可延数世之祀,然德文虽贤,不足以支倾厦。”这些评价共同勾勒出一位末代君主的复杂形象:他不是亡国的罪人,而是亡国的见证者。
今日回望那段历史,司马德文的名字或许不如曹操、刘备那般响亮,但他所代表的时代转折却意义深远。他的死亡,不仅意味着一个王朝的落幕,也预示着南北朝分裂局面的全面开启。此后百余年,南朝更迭频繁,北朝战乱不息,中国进入又一轮大分裂时期。
晋恭帝司马德文,这位在史书中常被一笔带过的末代皇帝,其实承载着厚重的历史重量。他的沉默退场,是一曲帝国黄昏的挽歌,也是新生政权铁血登场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