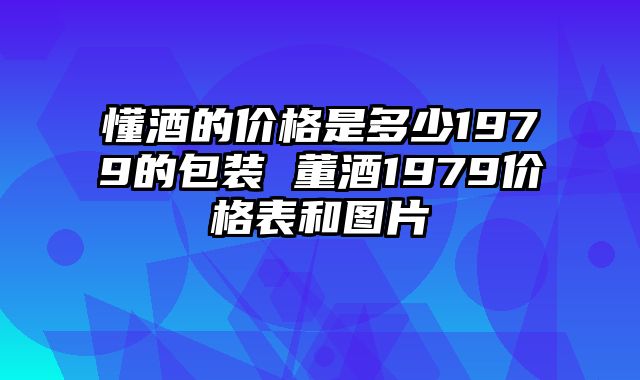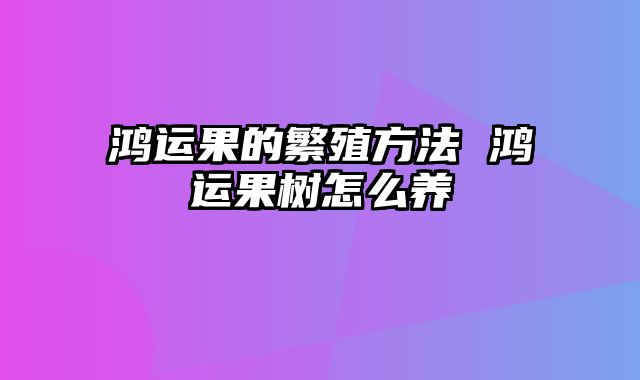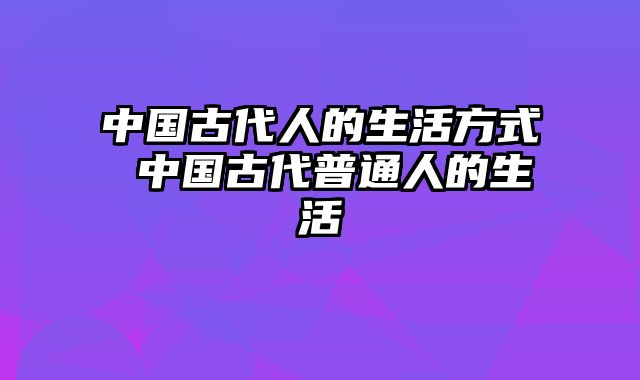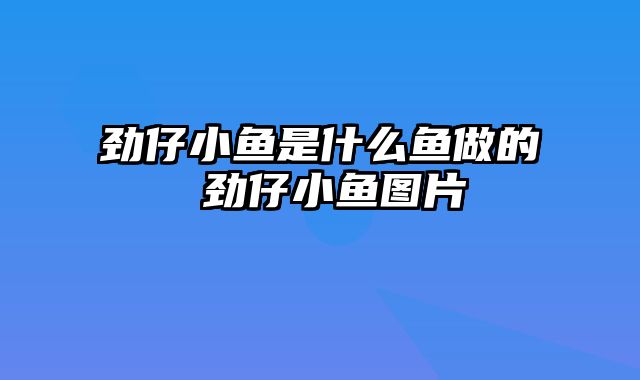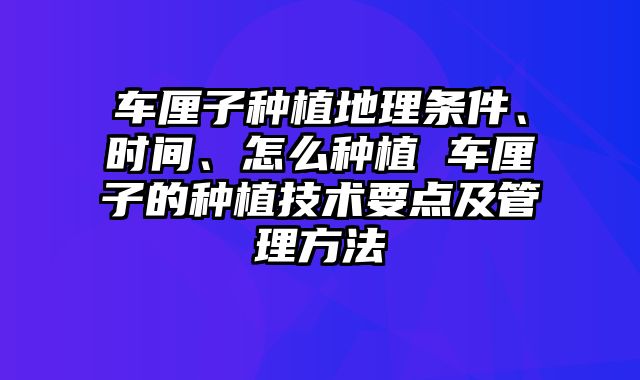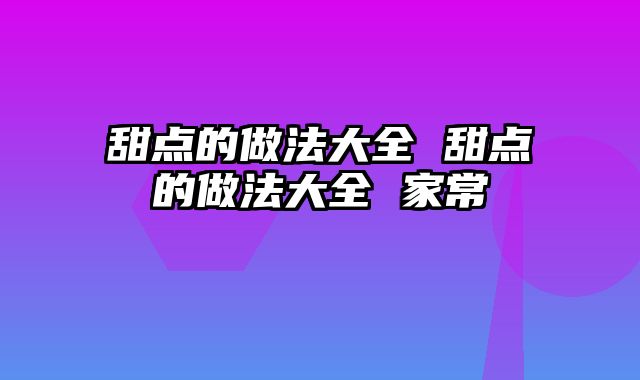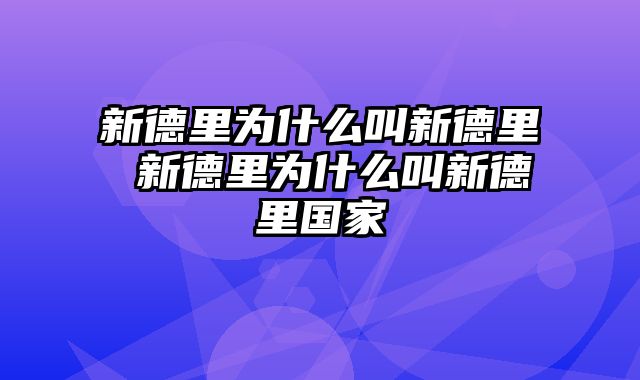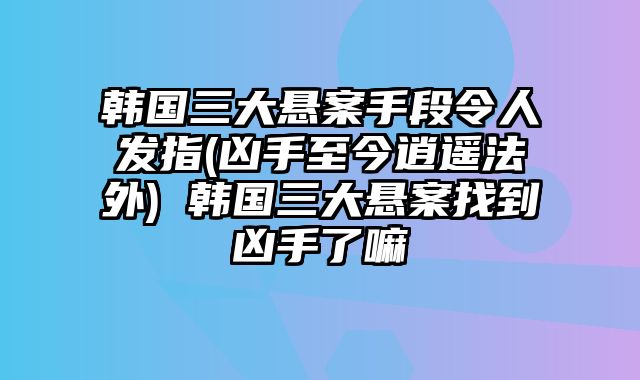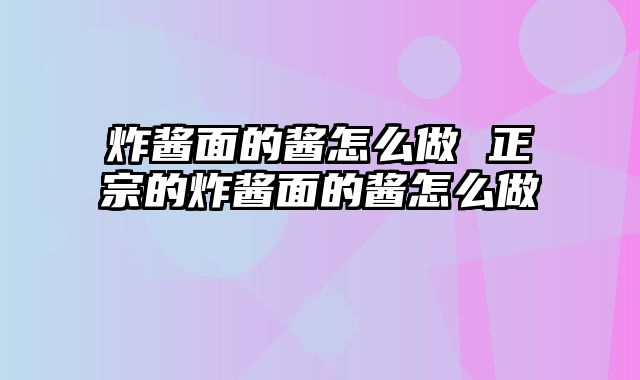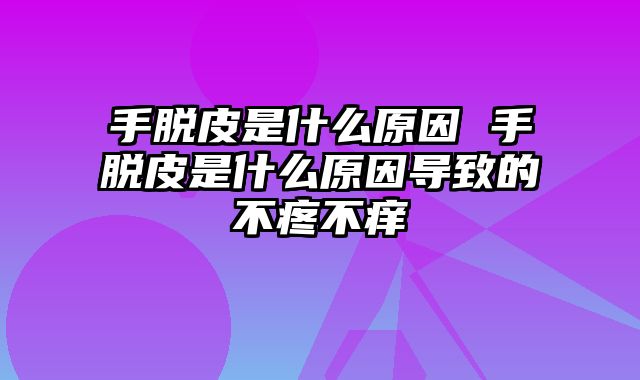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长河中,远古人类作为现代智人的直接祖先,承载着生命演化的关键密码。从非洲大草原上的早期直立行走到遍布全球的迁徙足迹,远古人类的历史不仅关乎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更深刻影响了语言、工具使用、社会结构乃至文化雏形的形成。考古学、遗传学与古环境研究的交叉融合,使我们得以逐步揭开这段跨越数百万年的壮阔图景。

远古人类的演化起点可追溯至约700万年前的非洲大陆。当时,气候变迁导致森林退缩,草原扩张,促使部分灵长类动物逐渐适应地面生活。这一生态压力推动了双足直立行走的出现,成为人类谱系与其他猿类分道扬镳的重要标志。目前已知最早的人类祖先之一是“乍得沙赫人”(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其化石发现于乍得地区,距今约700万年,虽颅骨形态仍具猿类特征,但枕骨大孔位置表明其可能已具备直立行走能力。
紧随其后的是“图根原人”(Orrorin tugenensis)与“地猿”(Ardipithecus),尤其是440万年前的“阿尔迪”(Ardipithecus ramidus)化石,提供了关于早期两足行走与树栖习性并存的关键证据。这些原始人科成员脑容量较小,平均不足400毫升,但已展现出社会协作与基本工具使用的萌芽。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约250万年前,人属(Homo)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最早的代表为“能人”(Homo habilis),意为“手巧的人”,因其与奥杜威石器文化的关联而闻名。能人脑容量提升至约600毫升,并开始系统性地制造简单石器,用于切割肉类与处理植物资源,标志着技术行为的开端。与此同时,肉类摄入比例上升,促进了大脑发育的能量供给,形成“营养-智力”正向循环。
随后出现的“直立人”(Homo erectus)则是人类演化史上的里程碑物种。约180万年前,直立人首次走出非洲,扩散至欧亚大陆,足迹遍及格鲁吉亚、中国周口店与爪哇岛。他们拥有更高的身材、更发达的脑容量(可达1000毫升以上),并掌握火的使用——北京猿人遗址中的灰烬层便是有力佐证。火不仅改善了食物消化效率,还延长了活动时间,增强了群体凝聚力,为后续认知飞跃奠定基础。
进入距今约50万年前,远古人类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海德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被认为是尼安德特人与现代智人的共同祖先,广泛分布于非洲、欧洲与西亚。他们建造简易住所、狩猎大型动物,并可能出现原始葬仪行为,暗示着对死亡的认知萌芽。
而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则在欧洲与西亚独立演化出高度适应寒冷环境的身体结构:粗壮骨骼、宽鼻腔以温暖空气、较大的视觉皮层。近年来的基因研究表明,现代欧亚人群平均携带1-4%的尼安德特人DNA,证明两者曾发生过杂交。尼安德特人制作莫斯特文化石器,使用赭石颜料,甚至可能埋葬死者并放置随葬品,显示出复杂的精神世界。
与此同时,在非洲大陆,一支新的力量正在崛起——智人(Homo sapiens)。约30万年前,摩洛哥杰贝尔依罗遗址出土的化石将现代人类起源时间大幅前推。智人具备更圆润的颅骨、较小的眉脊与突出的下巴,脑容量稳定在1350毫升左右。约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使其语言能力、抽象思维与符号表达突飞猛进,洞穴壁画、骨雕饰品、个人装饰品大量涌现,象征性文化全面爆发。
通过“走出非洲”第二次大迁徙,智人迅速取代或融合其他远古人种,最终成为地球上唯一幸存的人属物种。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征服,而是涉及气候变化、资源竞争、疾病传播与基因交流的复杂互动。例如,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虽在西伯利亚留下遗迹,却主要通过基因印记存在于现代大洋洲与东亚人群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远古人类的技术进步呈非线性发展。旧石器时代延续数百万年,工具样式变化缓慢;而进入新石器时代后,农业、定居、陶器与文字相继诞生,文明加速度显著提升。这种转变背后,是人口增长、环境压力与知识积累共同作用的结果。
今天,借助古DNA测序、同位素分析与三维成像等先进技术,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精度重构远古人类的生活图景。每一处化石发现、每一块石器拼合、每一次基因比对,都在丰富我们对自身根源的理解。远古人类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祖先,更是文化记忆的源头。他们的挣扎、创新与适应力,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深层的历史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