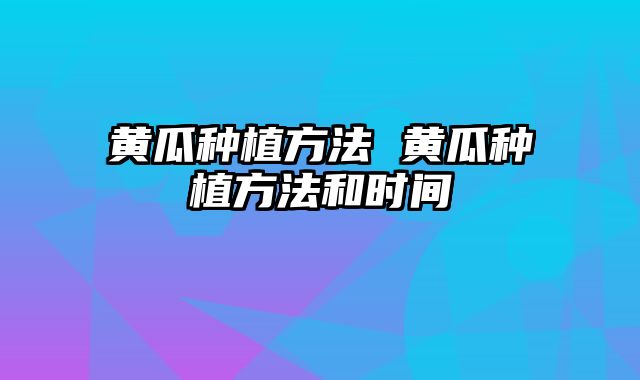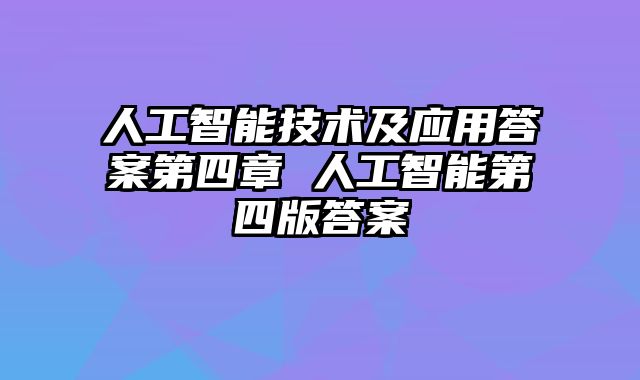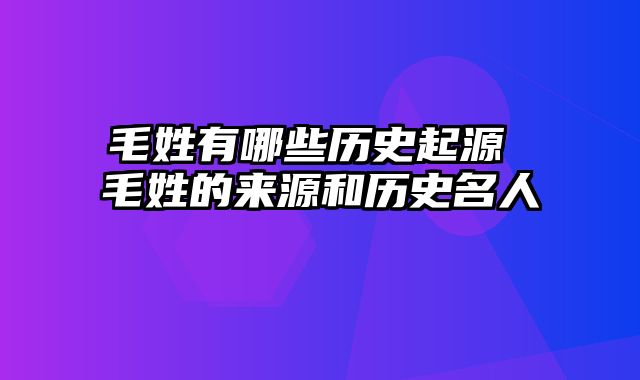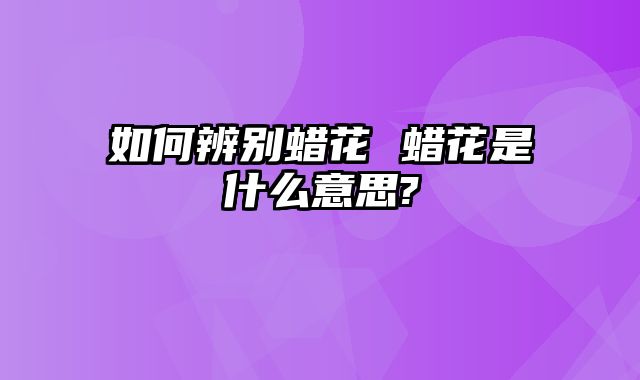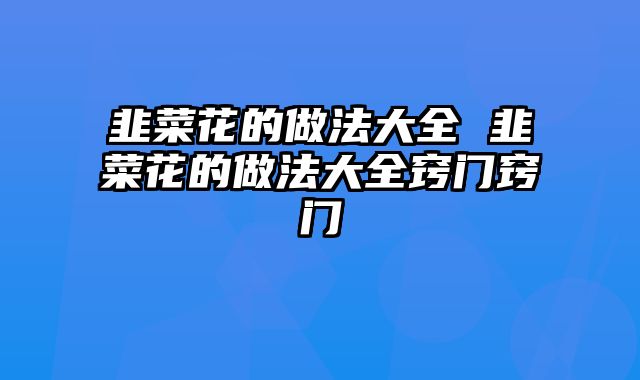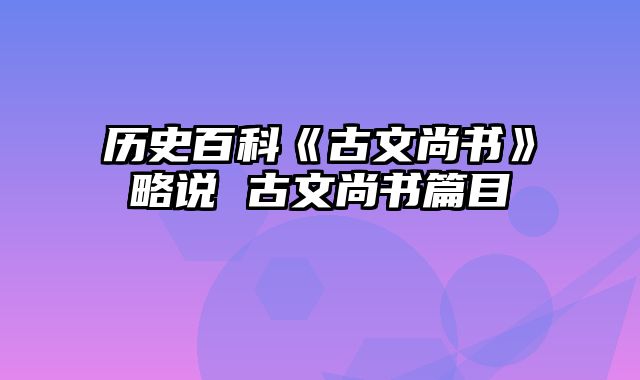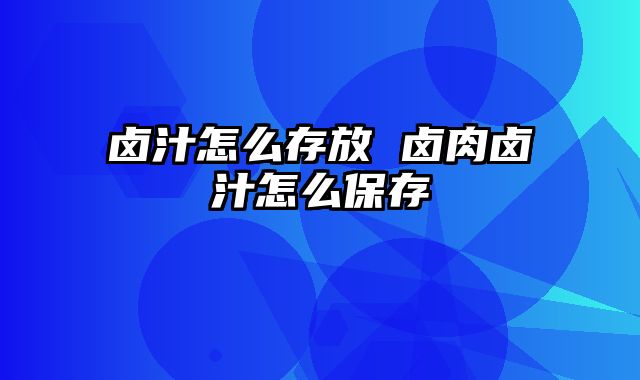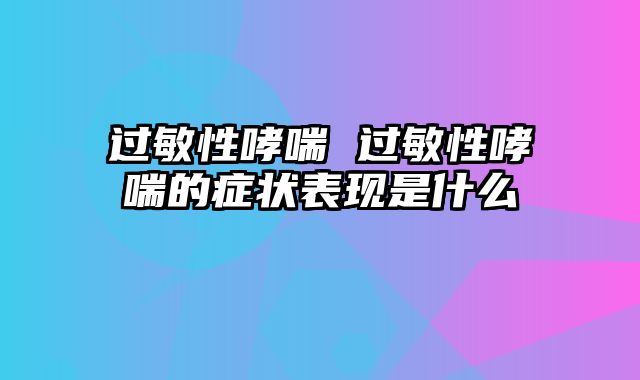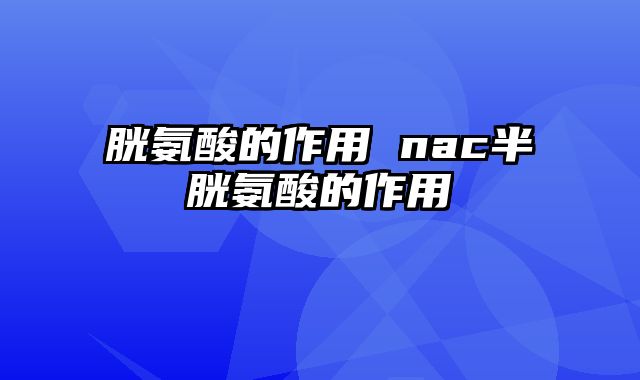太君”这一称谓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华东沦陷区频繁出现,表面看是日语“大人”(たいくん,taikun)或“队长”“长官”的音译误读,实则为日本侵略者精心设计的语言规训工具。它并非自然生成的民间敬语,而是日本军政当局通过伪政权、保甲制度、新民会及日语教育体系系统推行的符号暴力实践。要理解为何日本人强制中国人使用“太君”,必须超越字面音译的表层解释,深入殖民统治的话语机制、权力技术与心理控制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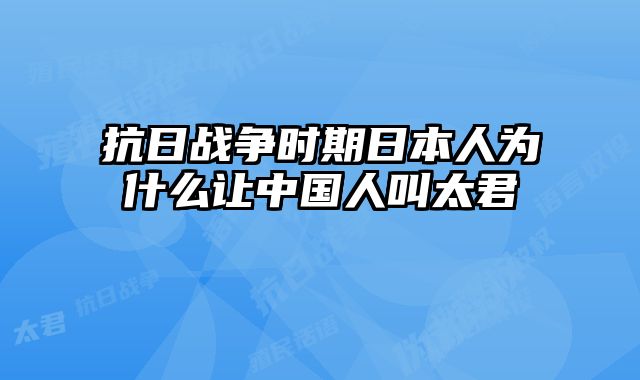
首先,“太君”一词并无对应日语原词。日语中对军官的正式称呼为“少佐”“大佐”“司令官”等军衔称谓,或敬称“様”(さま),而“たいくん”(taikun)在江户时代确指“征夷大将军”,属极高政治头衔,明治维新后已废止;战时日军基层军官绝无以“太君”自称之理。史料证实,该词最早见于1938年北平伪《新民报》社论,被刻意标注为“对皇军长官之尊称”,随后由华北政务委员会通令各市县学校、保甲、商会统一采用。其造词本质是“去语境化”的语言嫁接:截取日语“たい”(大)与“くん”(君,敬称后缀),拼合成汉语发音“tài jūn”,再赋予其虚构的“尊崇权威”内涵——既规避日语真实称谓所携带的制度性约束(如军衔等级),又制造出一种模糊却压迫性的主从关系。
这种语言操控服务于三重殖民目标。其一,消解中国人的主体性称谓体系。传统社会对官员称“老爷”“大人”,对军人称“长官”“将军”,皆嵌入儒家礼制与本土权力认知。而“太君”完全脱离中文语义网络,无法唤起任何文化认同,仅指向一个外来的、不可质疑的绝对权威。当一个河北农民被迫向持枪的日军小队长喊出“太君”时,他不仅在称呼对方,更在否定自身作为“人”的言说资格——因为这个词本身没有中文词根、不载于典籍、不通于乡俗,它的唯一合法性来自占领者的意志。
其二,构建日常化的服从仪式。日本在沦陷区推行“亲善”政策,要求学校晨会向东京遥拜、商铺悬挂日章旗、市民行九十度鞠躬礼。“太君”称谓被纳入这套身体规训体系:伪警察须在报告时加称“太君”,学生作文须以“太君教导我们”开篇,甚至菜市场讨价还价若被日兵听见,摊主亦需立即改口。1943年天津英租界档案记载,一名卖豆腐老人因未及时称“太君”遭扇耳光,理由是“失却敬意即失却生存资格”。这种高频、琐碎、无处不在的语言勒令,将暴力内化为习惯,使屈辱成为呼吸般的自然状态。
其三,瓦解抗日话语的情感基础。中共地下党在冀中根据地编印的《反奴化手册》明确指出:“呼‘太君’者,犹自断脊骨。”因为“君”在中文里本含道德期许(如“君子”),而“太”字叠加,反而扭曲为一种畸形崇拜。当青少年被强迫书写“太君恩如父母”作文时,传统孝道伦理被劫持为殖民效忠工具;当汉奸宣传队演唱《太君爱我如赤子》时,民族情感被置换为依附幻想。语言学家王力1946年在《沦陷区语言变异研究》中痛陈:“太君非词也,乃刺入民族神经之毒针。”
值得深思的是,并非所有沦陷区均强制使用此词。东北伪满洲国推行“满语”称谓体系,多用“指导官”“协和员”;上海租界区因国际舆论压力,日军默许使用“先生”或“长官”。唯独在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核心区,“太君”被列为“思想肃正”考核指标,村公所墙报设“敬称执行榜”,未达标者罚粮减配。这揭示其本质:不是语言现象,而是政治镇压的技术参数。
抗战胜利后,“太君”迅速退出公共话语,但其历史幽灵并未消散。20世纪80年代影视作品为增强戏剧冲突大量使用该词,反而将其符号化、扁平化为“鬼子标配台词”,遮蔽了它曾作为精密殖民装置的真实功能。今天重审“太君”,不是为了复述仇恨,而是辨识语言如何被武器化——当一种称谓被强加为生存前提,它便不再是交流媒介,而成为测量奴役深度的标尺。真正的历史清醒,在于看清每个被权力篡改的词语背后,都站着无数沉默弯腰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