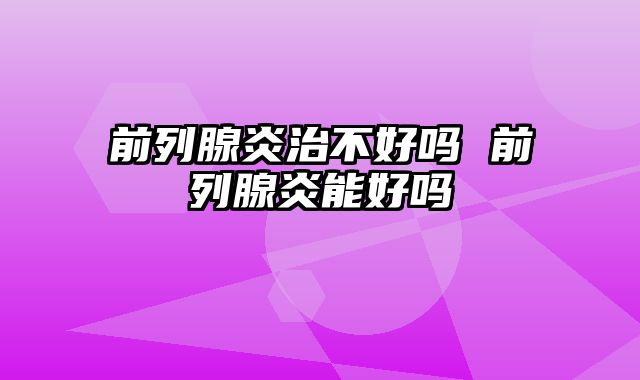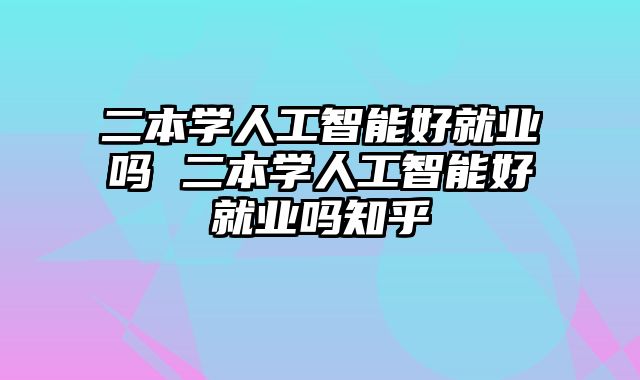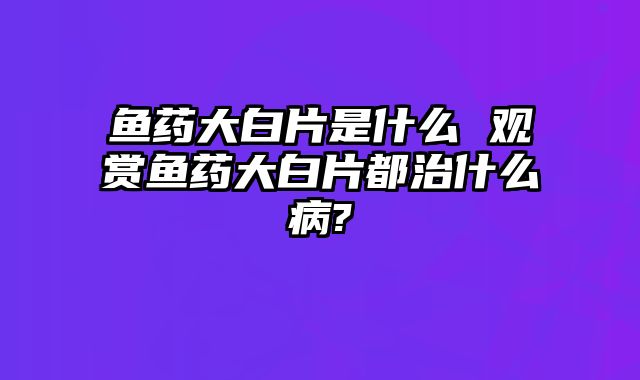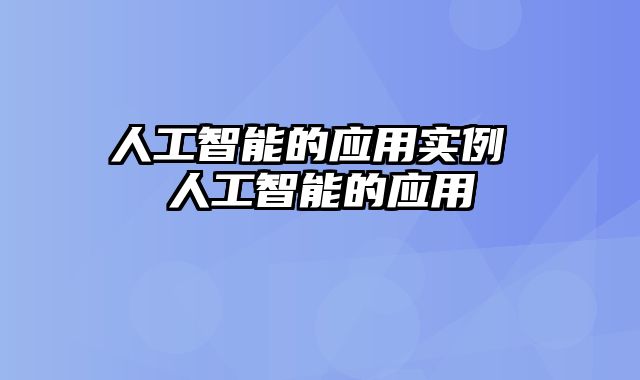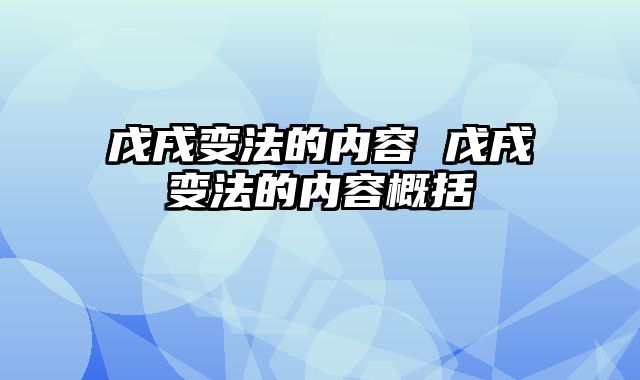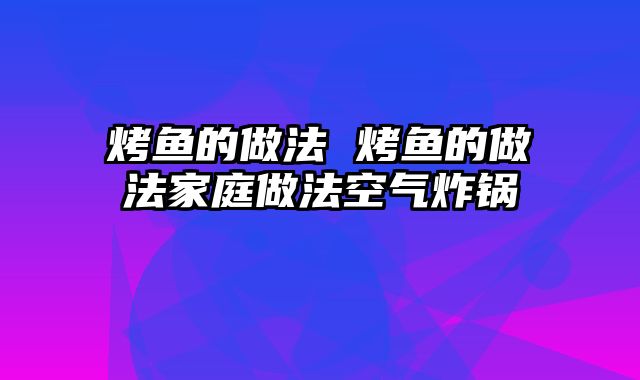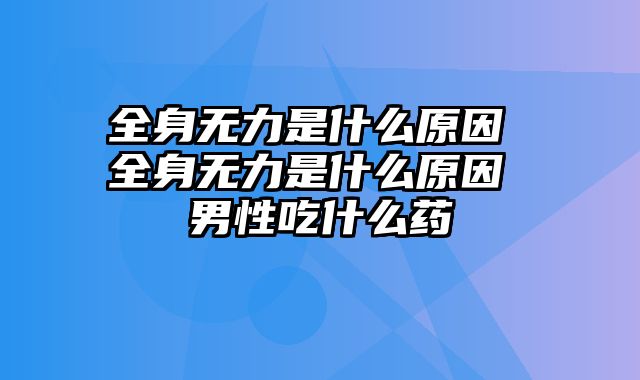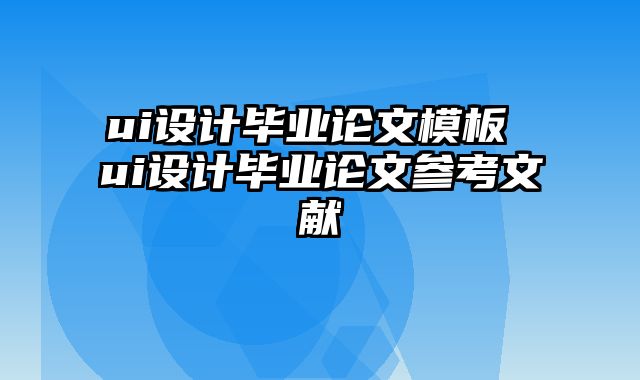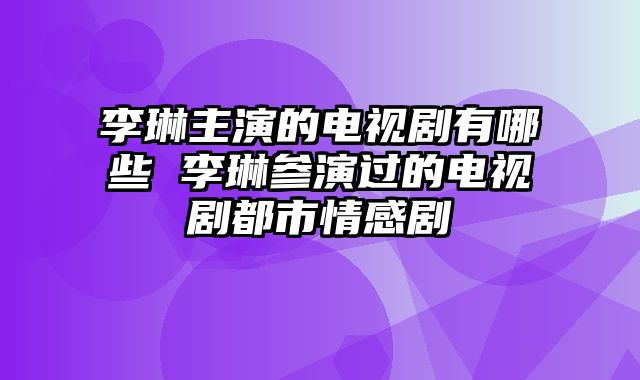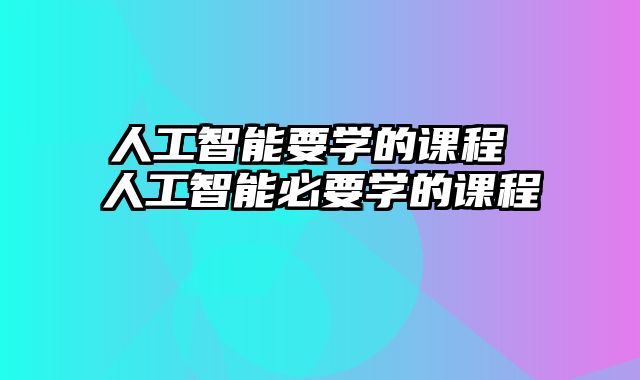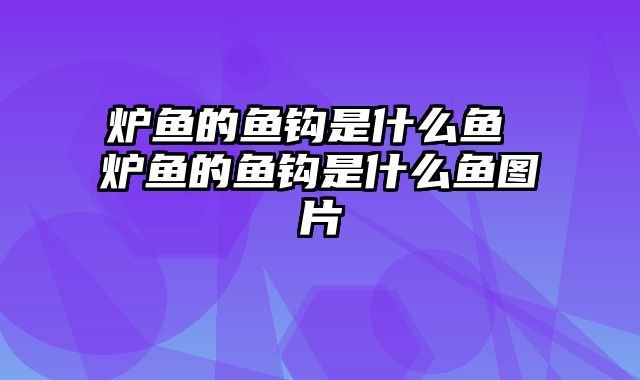贾陀活跃于公元755年至780年间,正值安史之乱前后。此时长安荐福寺、大兴善寺为密宗弘法重镇,不空以国师身份主持译场,贾陀为其核心助译僧之一。《大唐贞元续开元释教录》明确记载:“上都大兴善寺沙门贾陀,参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二卷,校勘梵夹,审音析义,功居其半。”值得注意的是,此经虽署不空主译,但现存敦煌本(如P.2273)多处朱笔批注显示,贾陀不仅负责语音转写,更对“五智如来”“四印曼荼罗”等核心概念的汉语诠释提出系统性修订意见,强调“智”非仅认知之智,而是“本觉自性之光”的当下显发,这一理解明显区别于早期玄奘唯识学路径,而贴近后来惠果所确立的“即身成佛”理论雏形。

除译经外,贾陀亦是密法实践的重要推动者。日本入唐求法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追述,开成五年(840年)他在五台山佛光寺得见一幅残破壁画,榜题“贾陀禅师结印说法图”,画中僧人结金刚界大日如来根本印,身绕五色光焰,足踏莲花月轮——此图像风格与同期青龙寺惠果所绘曼荼罗高度一致,暗示贾陀或曾参与早期密教图像范式的确立。更关键的是,敦煌遗书S.5540《金刚顶经略出念诵经》末尾有墨书小字:“大历八年(773)岁次癸丑,贾陀于终南山圭峰精舍依梵本重勘,去繁存要,以便行者。”这说明他不仅精通理论,更注重密法在地化传播,主动删减繁复仪轨,提炼适合中土僧俗修持的简易念诵体系,堪称唐代密教“实践转向”的早期代表。
关于贾陀的卒年与归宿,史料语焉不详。《宋高僧传》称其“晚岁隐终南,莫知所终”,而吐鲁番出土回鹘文《金刚顶经》残片(编号TIIY 56)背面有粟特文题记:“此本依贾陀阿阇梨口授而写,时大唐建中三年(782)”,证明其至少活至德宗初年。另有学者据敦煌P.3849《诸佛心印陀罗尼经》抄本中“贾陀法师付授”印章推断,他可能在不空圆寂(774年)后成为独立传法阿阇梨,但因未获朝廷正式册封,故未列入官方僧录,致其事迹湮没。近年西安西郊出土的唐大历年间砖塔铭(2019年长安区韦曲M12)提及“故大兴善寺翻经沙门贾陀灵塔”,虽塔身已毁,却为其实存提供了考古实证。
贾陀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代表了唐代密宗从“译经主导”向“修法主导”过渡阶段的关键中介。他既忠实地传递不空所承印度晚期密教精髓,又以汉语思维重构概念体系;既维护梵本权威,又大胆调适仪轨以应中土根机。其工作无形中为惠果集大成、空海携法东传铺平了语言与实践的道路。今日重审贾陀,不仅是填补中古佛教史的人物缺环,更是理解密教何以能在华夏土壤扎根、演化乃至反哺东亚文明的重要锁钥——他不是光芒万丈的太阳,却是密宗长河中一道沉潜而有力的暗流。
在当代学术视野下,贾陀研究正迎来新契机。随着敦煌、吐鲁番、黑水城多语种密教文献的持续刊布,以及数字人文技术对写本题记、印章、笔迹的比对分析,这位“被遗忘的阿阇梨”正逐步褪去模糊轮廓。他的存在提醒我们:一部宗教传播史,从来不只是大师与经典的故事,更是无数无名而笃实的译者、校者、行者以生命践行所共同编织的经纬。
贾陀,唐代中期一位鲜见于正史却屡现于佛教典籍与敦煌遗书中的密教僧人,其名虽不若不空、惠果般广为人知,却是开元天宝年间汉地密宗传承谱系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七、《宋高僧传》卷一补遗及敦煌写本P.2012《大日经义释序》题记所载,贾陀(音近“迦陀”,梵名可能为Gata或Jata,学界尚无定论)为中天竺来华僧人不空三藏(705–774)门下“内院十哲”之一,专精《大日经》《金刚顶经》义理及坛场仪轨,尤擅梵汉对译与密法实修。他并非印度本土高僧,而极可能是中亚粟特地区通晓梵语、悉昙体与汉语的双语宗教精英——这一判断基于其名在梵文文献中无直接对应,却频繁出现在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密教残片及敦煌S.2659号《金刚顶经瑜伽修习法》抄本校勘题记中,署名“沙门贾陀奉诏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