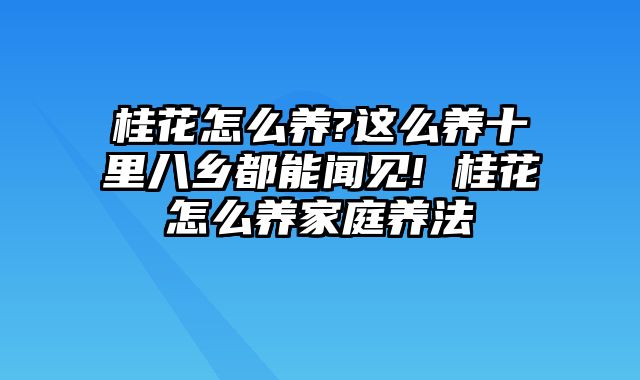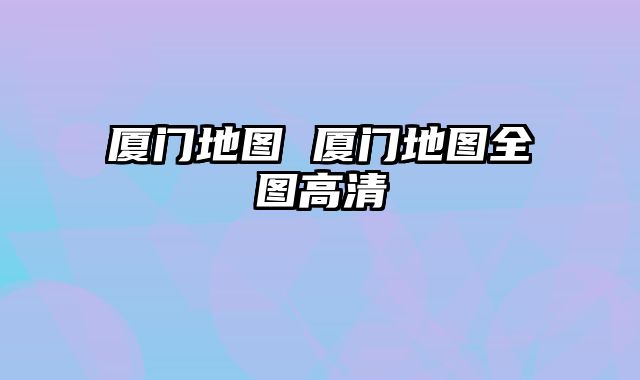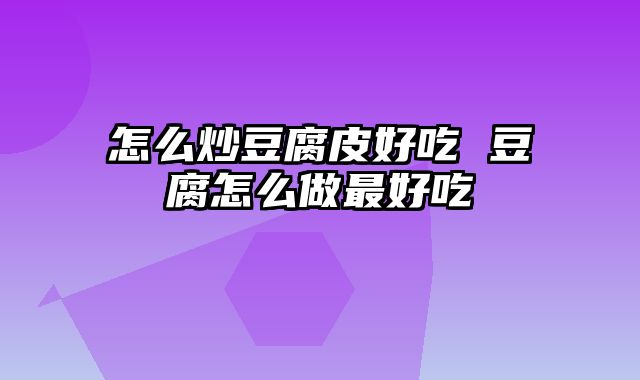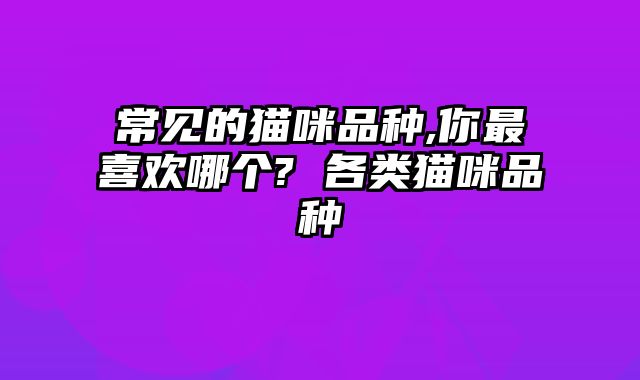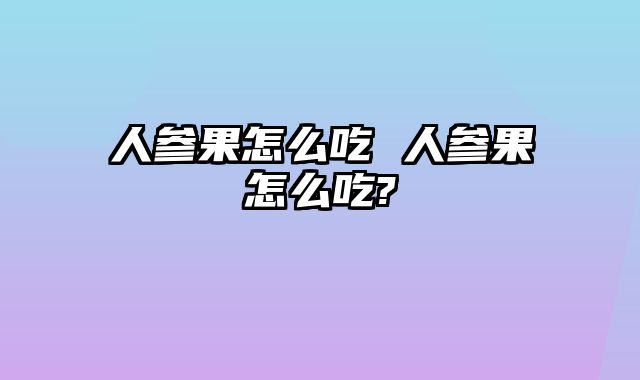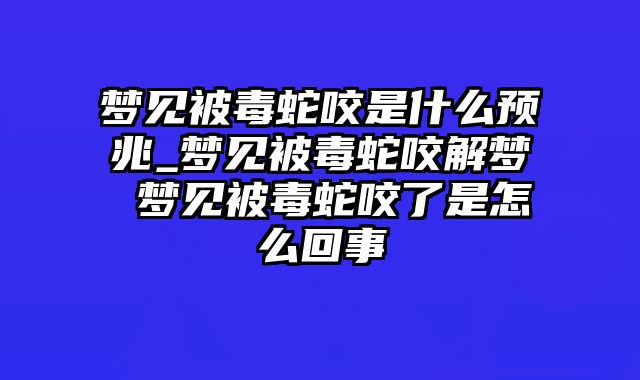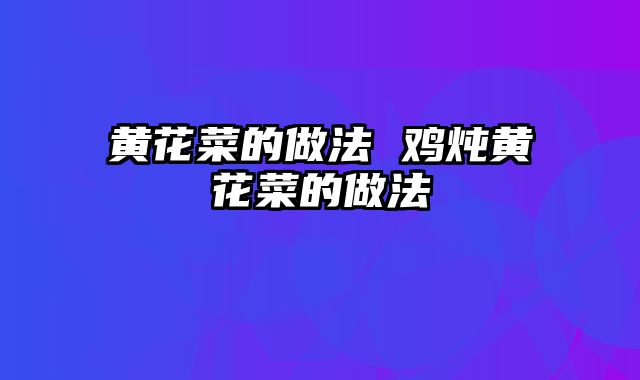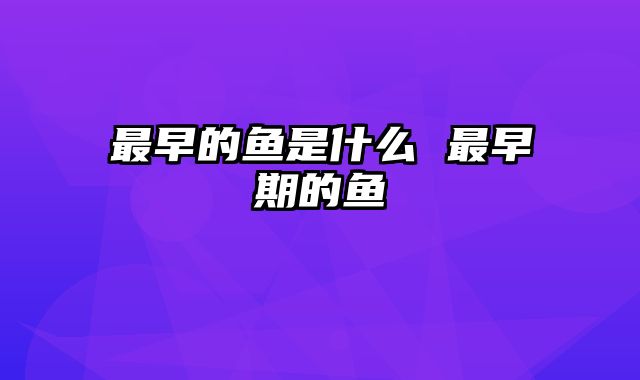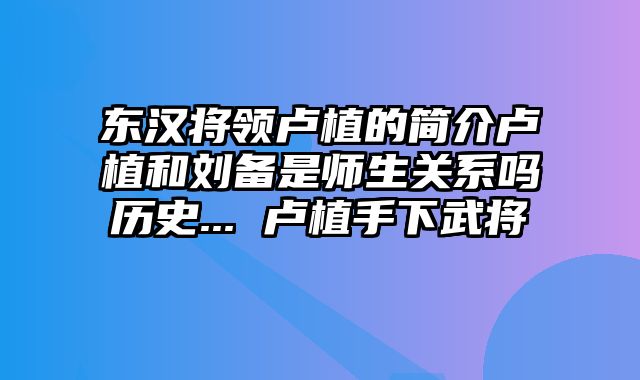英国绅士风度并非一种浮于表面的礼仪表演,而是植根于中世纪封建制度、文艺复兴人文思想、17世纪清教伦理、18世纪启蒙理性与19世纪维多利亚道德体系多重历史层积之上的复杂文化范式。其核心不在于“戴礼帽、持手杖、为女士开门”的刻板印象,而在于一套以自律、责任、隐忍与尊严为内核的行为哲学——它既是社会阶层流动的通行证,也是道德自我规训的日常实践。

追溯其源头,可上溯至14世纪《爱德华三世宪章》中对“gentleman”一词的首次法律界定:指拥有年收入20英镑以上土地、无需从事体力劳动、具备骑士精神潜质的自由男性。此时“绅士”仍是身份标签,强调血统与财产。但百年战争与黑死病后,旧贵族大量凋零,新兴乡绅(gentry)通过教育、司法任职与地方治理崛起,开始将“gentle”(温和)与“man”(人)重新组合,赋予其道德内涵。托马斯·伊莱亚斯在《宫廷与社会》中指出,16世纪伊丽莎白时代宫廷手册如《廷臣论》的英译本流行,促使“彬彬有礼”(courtesy)从宫廷特权转向可习得的公民素养。
真正完成绅士风度的伦理转化是在17世纪。清教徒强调“内在圣洁外显于行为”,约翰·班扬《天路历程》中基督徒的谨慎、谦卑与坚韧,悄然重塑了绅士气质:克制激情比彰显勇气更需力量,履行职责比追求荣誉更显高贵。这一转向在洛克《教育漫话》(1693)中达到理论高峰。洛克断言:“绅士教育之首务,非学问,而在德行;非雄辩,而在判断;非记忆,而在审慎。”他主张以骑术、舞蹈、击剑等身体训练培养镇定,以古典研习与旅行见闻涵养视野,以日常微小义务(如准时赴约、信守诺言)锤炼意志——绅士由此成为“理性自律的具身化”。
18世纪启蒙运动进一步去贵族化。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在《漫步者》中反复申明:“真正的绅士,是无论身处沙龙或市集,皆能保持同等庄重与善意之人。”此时咖啡馆、文学社团与共济会成为新绅士的养成所:在这里,出身让位于谈吐,爵位服从于逻辑。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揭示其心理机制——“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内化为良知,使绅士在无人注视时亦能自我监督。这种内省性,正是绅士风度区别于单纯礼貌的本质。
维多利亚时代则将其制度化与仪式化。公立学校(如伊顿、哈罗)将“团队精神、体育道德、沉默坚忍”列为校训;《泰晤士报》专栏日日刊载“得体行为指南”;铁路时刻表要求全民守时,电报普及迫使语言精简克制。最典型的体现是“不抱怨”(stiff upper lip)原则:克里米亚战争中军官在战壕里读诗、印度兵变后殖民官员在焚毁宅邸前整理领结——表面是压抑情感,实则是将个体痛苦转化为对秩序与责任的无声捍卫。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后来指出,这种“洁净与危险”的边界意识,本质是用行为规范对抗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绅士风度始终伴随张力。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借郝薇香小姐讽刺伪绅士:皮普靠不义之财获得外表教养,却丧失本真;而铁匠乔·加格里虽粗粝,其诚实与宽厚反具绅士魂魄。萧伯纳《卖花女》更尖锐揭示:语音训练可模仿上层口音,但真正的绅士性在于对弱者的尊重——希金斯教授终其一生未学会向女仆说“谢谢”。20世纪以来,绅士风度持续嬗变:丘吉尔的雄辩与自嘲、阿滕伯勒的博物学热忱、甚至当代威廉王子参与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服务,均表明其内核已从阶级符号蜕变为公民美德的现代表达——尊重差异、承担责任、保持谦抑、行动胜于言辞。
今日重审英国绅士风度,绝非要复刻维多利亚时代的拘谨,而是汲取其将道德抽象为日常实践的智慧。当算法推送加剧情绪极化、社交媒体鼓励即时宣泄之时,“延迟反应”“倾听先于反驳”“为他人保留体面”这些古老准则,恰成数字时代的稀缺修养。绅士风度真正的遗产,从来不是一套过时的举止守则,而是一种清醒的自觉:在任何境遇中,选择成为自己所相信的价值的活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