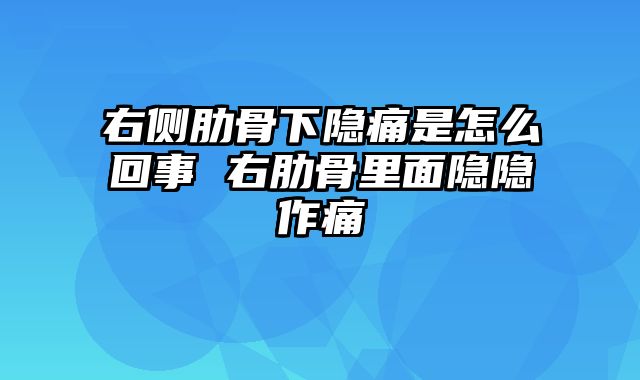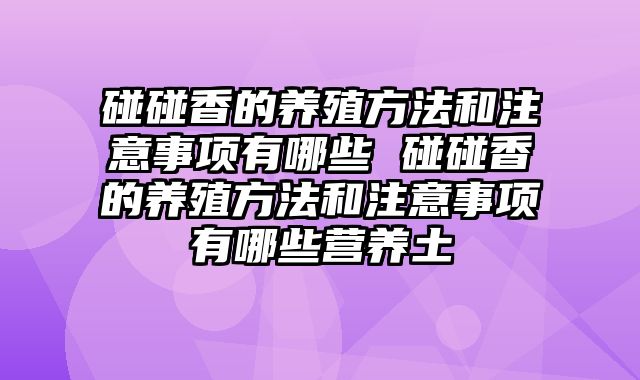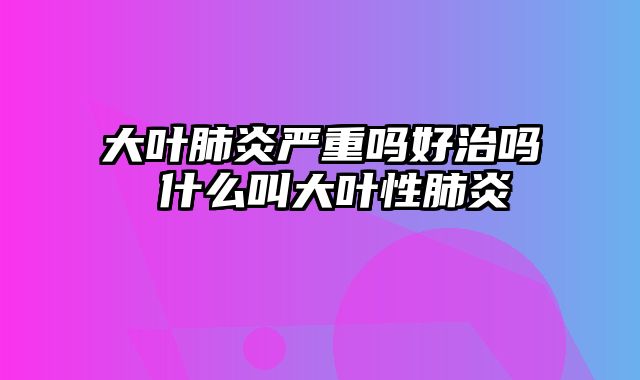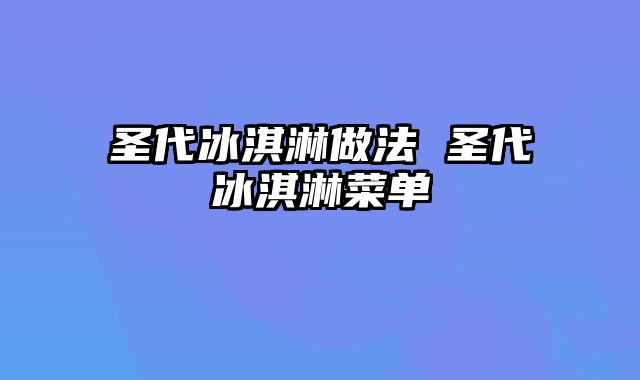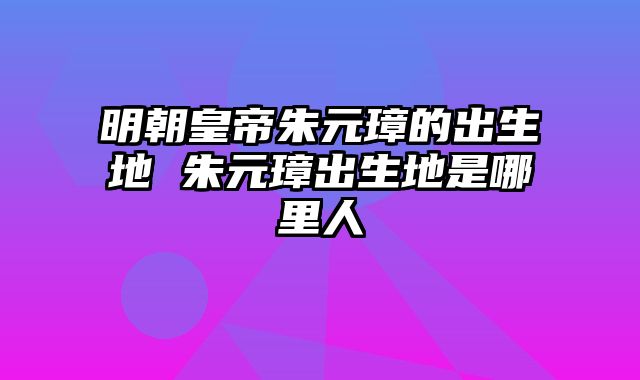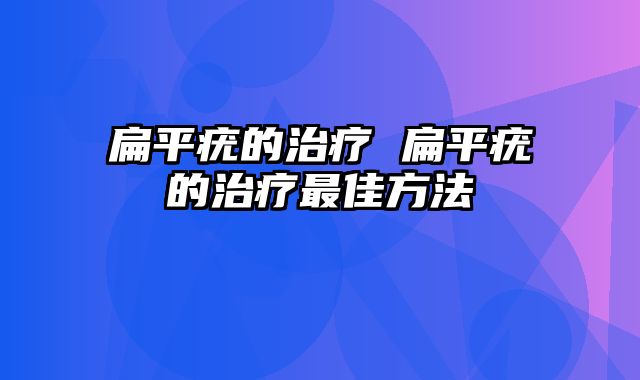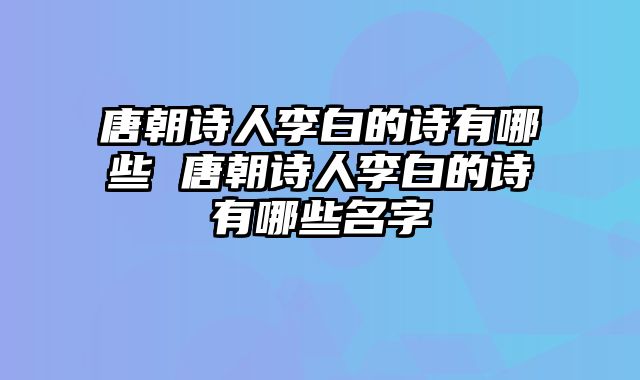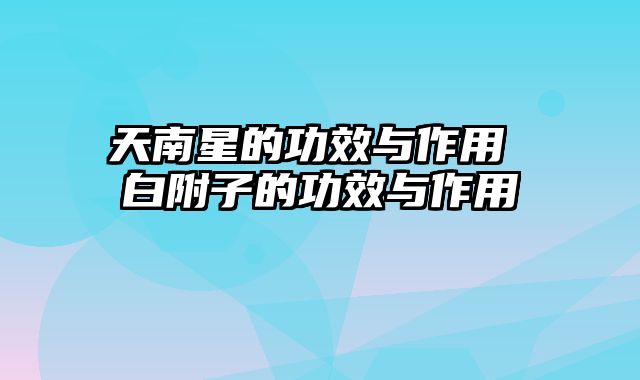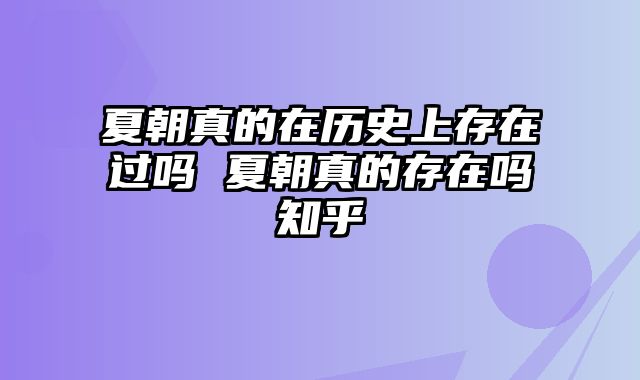1904年春,喜马拉雅山北麓的江孜古城笼罩在凛冽寒风与战争阴云之中。一场关乎主权、信仰与民族尊严的殊死抵抗,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腹地悄然拉开帷幕——这便是近代中国边疆史上震撼人心的江孜保卫战。它并非孤立的军事冲突,而是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1903–1904)的高潮与转折点,更是西藏地方军民在清廷中央权威严重弱化背景下,以血肉之躯捍卫领土完整的自觉抗争。

事件肇始于1903年12月,英国印度总督寇松以“通商谈判”为名,派遣荣赫鹏上校率3000余人的武装使团,携马克沁机枪、阿姆斯特朗山炮等先进装备,强行越过则里拉山口,侵入西藏亚东。清廷驻藏大臣有泰消极避战,屡令藏军“勿启衅端”,而达赖喇嘛十三世亦因政局动荡暂避库伦。在此权力真空与战略失序之际,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与僧俗民众并未屈服。1904年4月,英军攻陷帕里后直扑江孜——这座扼守拉萨南大门、控引年楚河谷的战略枢纽。江孜宗山(宗政府所在地)依山而建,石砌堡垒居高临下,成为天然要塞;当地僧兵、民兵及部分正规藏军迅速集结,由代本(军官)朗色林·班觉晋美、拉加里王公及江孜宗本洛桑顿珠等组织防御,动员数千民众运粮、筑工事、熔铸土炮,甚至将寺院铜钟熔铸为弹丸。
5月3日,英军首次进攻江孜宗山受挫;6月26日,经数周围困与炮火轰击,英军集中12门山炮猛轰宗山城堡,藏军以火绳枪、弓箭、滚木礌石顽强还击,击毙英军数十人,包括副指挥官麦克唐纳少校。尤为悲壮的是,7月5日至6日,英军发动总攻,藏军弹尽援绝,仍持刀矛肉搏。据英军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记载:“他们没有现代武器,却从每一道墙缝、每一处垛口射出子弹……当最后一批战士退至宗山顶部,他们砸毁火药库,引燃烈焰,宁死不降。”7月7日凌晨,残存守军数百人在宗山绝顶集体跳崖或自焚殉国,无一人被俘。江孜沦陷,但抵抗未止:此后藏军转战白朗、浪卡子,持续袭扰英军补给线,迫使荣赫鹏不得不分兵驻守,延缓其进逼拉萨的步伐。
江孜保卫战的历史意义远超军事层面。它是西藏人民首次以近代民族意识为内核的大规模自主防卫行动,打破了传统“政教合一”体制下仅依赖中央调停的被动逻辑;其惨烈牺牲催生了西藏近代爱国思潮的萌芽,《江孜纪略》《雪域忠魂》等民间叙事在卫藏广为传诵;同时,它也成为清末边疆危机的重要镜鉴——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虽确认中国对西藏主权,却默许英国在藏特权,暴露清廷治边能力的系统性衰竭。今日江孜宗山遗址立有“江孜抗英纪念碑”,山巅残存的炮台、弹孔、断垣与经幡交织,无声诉说着那场没有胜利勋章却赢得历史敬意的战斗。它提醒世人:在帝国主义瓜分狂潮席卷东亚的至暗时刻,青藏高原的孤勇者以生命重申了一个古老文明不可让渡的底线——土地可寒,民心不可侮;山河可蔽,主权不可蚀。
这场持续近三个月的保卫战,参战藏军约1.4万人,伤亡逾5000人,英军阵亡203人、伤400余人(数据据英方战报与中方档案交叉印证)。值得注意的是,守军中包含大量宁玛派、萨迦派僧人,他们脱下袈裟执戈而战,体现宗教热忱与家国情怀的高度统一;民间更流传“江孜三宝”之说——宗山石、年楚水、抗英魂,成为西藏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符号。2006年,江孜宗山抗英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纪念江孜保卫战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学界共识日益清晰:它不是“闭关自守的愚昧抵抗”,而是前现代国家在主权意识觉醒初期,面对不对称战争所迸发的伦理韧性与文化尊严。
历史从不因战败而失重,恰如江孜宗山的沉默——它不高耸入云,却以嶙峋风骨撑起一个民族的记忆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