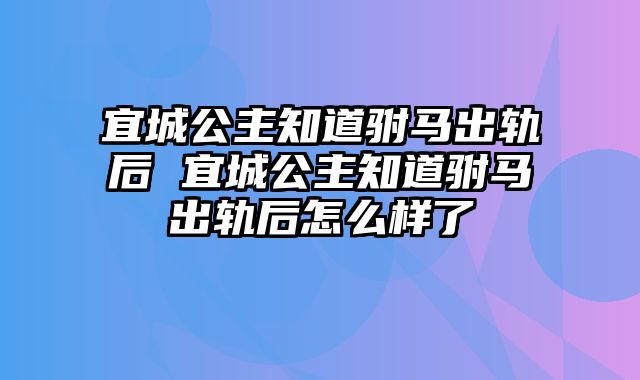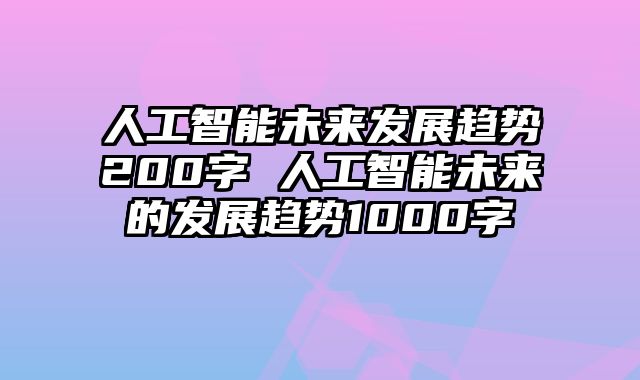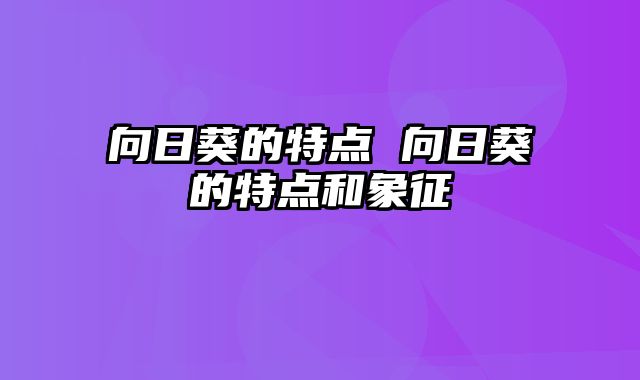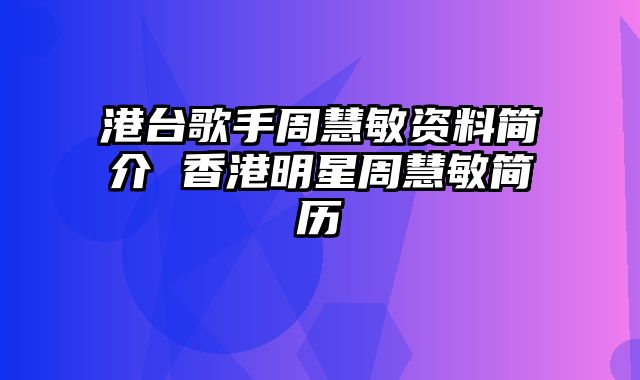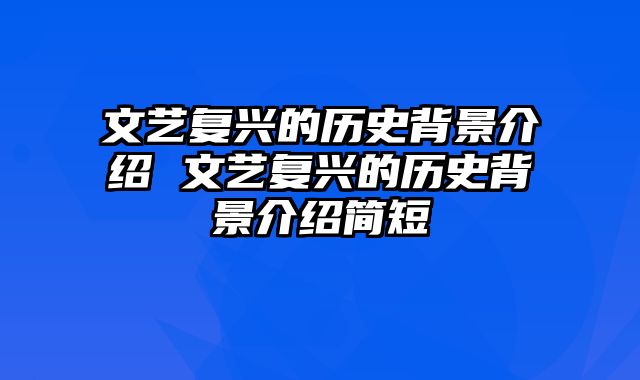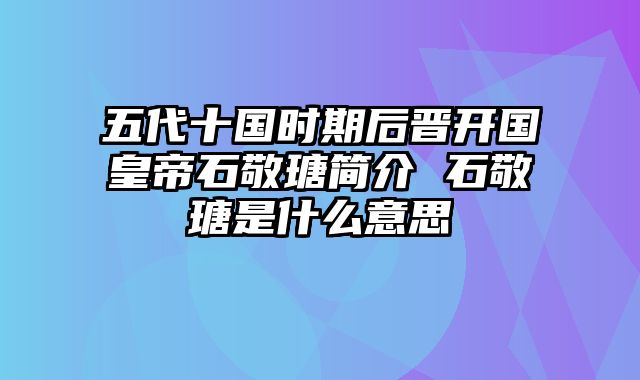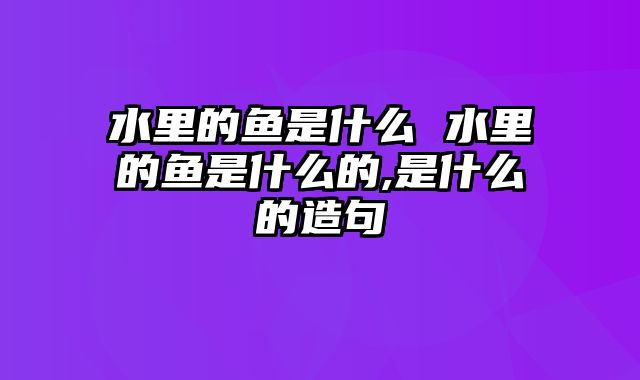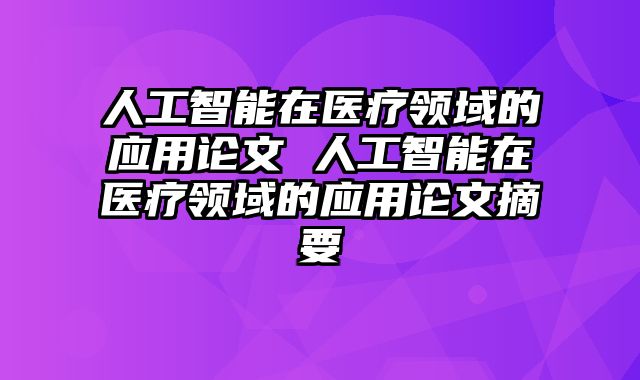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年),唐朝第七位皇帝,开创“开元盛世”,将大唐推向封建文明的巅峰;晚年却因宠信奸佞、沉溺享乐而酿成“安史之乱”,致使帝国由盛转衰。他生命的终结,并非猝然暴毙或战乱罹难,而是在政治失势、亲情崩解与精神孤寂中缓慢凋零的悲剧性终局——公元762年5月3日(宝应元年四月初五),这位曾执掌帝国四十四年的天子,在长安太极宫神龙殿悄然离世,终年七十八岁。

唐玄宗之死,需置于安史之乱后复杂的政治重构中理解。755年安禄山起兵后,玄宗仓皇西逃至马嵬驿,禁军哗变,逼其赐死杨贵妃、诛杀宰相杨国忠,威信尽丧。太子李亨于灵武自行即位,是为唐肃宗,遥尊玄宗为“上皇天帝”。此举虽属危局权宜,却在法统层面完成了权力移交——玄宗自此失去实权,沦为象征性存在。
返京后,玄宗被安置于兴庆宫,表面尊崇,实则渐受监控。肃宗宠信宦官李辅国,后者视太上皇为潜在威胁。760年七月,在李辅国策划下,玄宗遭“护送”迁居太极宫(西内),形同软禁。随侍旧臣如高力士、陈玄礼被贬斥流放,亲信宫人悉数更换,连昔日最信任的妹妹玉真公主亦不得自由探视。史载“上皇不怿,因不茹荤,浸以成疾”,精神抑郁直接诱发身体衰竭。
医学角度而言,玄宗晚年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征兆。《旧唐书》称其“寝疾累旬”,《资治通鉴》载其“气喘不能言,目不能视”,符合高龄老人急性心力衰竭或缺血性卒中表现。现代学者结合史料推断,其长期酗酒(尤喜饮葡萄酒)、肥胖(开元后期体重明显增加)、缺乏运动及情绪剧烈波动(马嵬之变、肃宗即位、高力士流放等接连打击),构成典型心血管病高危因素。762年春,玄宗病情急剧恶化,出现持续性呼吸困难、意识模糊与肢体偏瘫症状,最终在孤立无援中辞世。
值得注意的是,玄宗去世时间点极具政治敏感性:他病逝于宝应元年四月初五,仅十三日后——同年四月十八日,唐肃宗亦驾崩。父子相继离世,引发后世诸多揣测。但新出土的唐代墓志铭(如《高力士墓志》)与敦煌文书P.2642《肃宗实录残卷》证实,玄宗确系自然病亡,肃宗之死则源于久患风疾(中风后遗症)与惊悸劳神,并无毒杀或政变痕迹。所谓“肃宗闻父崩而惊厥暴卒”属后世小说演绎,正史未采信。
玄宗身后哀荣隆重却暗含疏离。肃宗本拟“号泣不视事”,但因朝议压力,仅辍朝三日,谥号“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玄”取“深远幽微”之意,隐含对其晚年昏聩的委婉批评。其葬于泰陵,依山为陵,规模较初唐诸帝缩减,陪葬者仅元献皇后杨氏(肃宗生母)一人,无一子一女附葬,折射出家庭关系的彻底破裂。更耐人寻味的是,代宗李豫(肃宗长子)即位后,立即为高力士平反,追赠扬州大都督,却始终未恢复玄宗朝核心文臣张说、张九龄等人的全部名誉,暗示官方对开元—天宝政治遗产采取选择性继承策略。
从历史纵深看,玄宗之死标志着盛唐精神的物理性终结。他临终前未能见到收复洛阳的捷报(史思明已于761年被杀,叛军瓦解),亦未见证郭子仪率军重返长安的盛况。他的生命熄灭于王朝重建的黎明前夕,恰似一个时代落幕时最后一缕余晖。白居易《长恨歌》中“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的意象,虽为文学虚构,却精准捕捉了这位老人在西内深宫中辗转反侧、追忆华清池歌舞与马嵬坡秋雨的永恒怅惘。
今天回望玄宗之死,早已超越个体生死范畴。它警示着权力巅峰的脆弱性——再辉煌的功业,若缺乏制度制衡与自我警醒,终将被人性弱点反噬;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皇权交接中温情面纱下的冰冷逻辑:当“君权神授”遭遇现实政治博弈,“孝道”与“法统”常成为权力清洗的修辞工具。泰陵松柏至今苍翠,而玄宗留在史册中的,不仅是“九重城阙烟尘生”的悲怆,更是盛衰辩证法最沉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