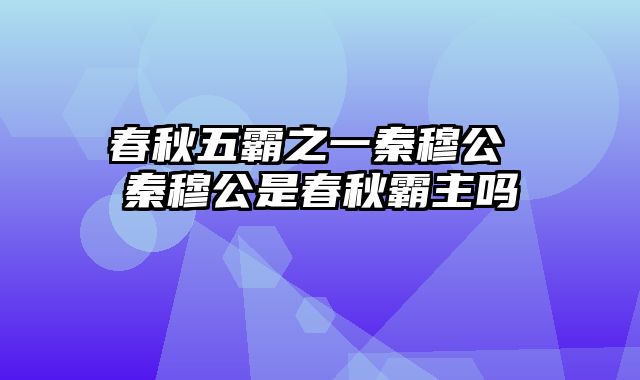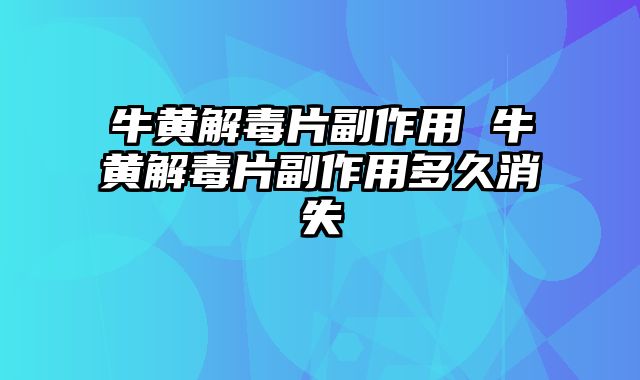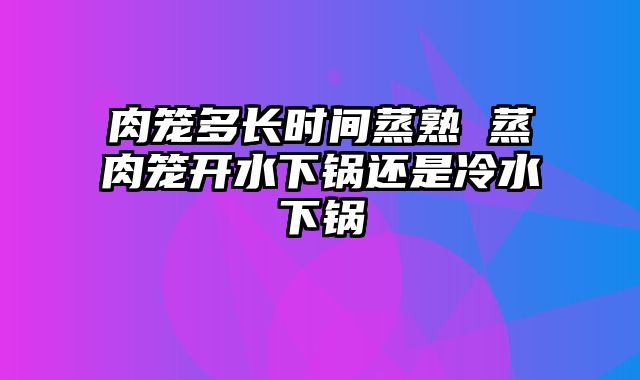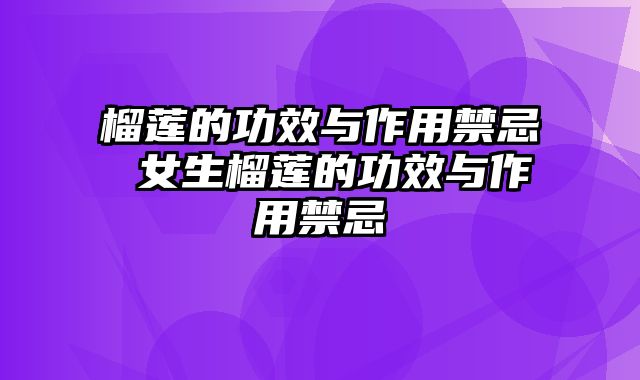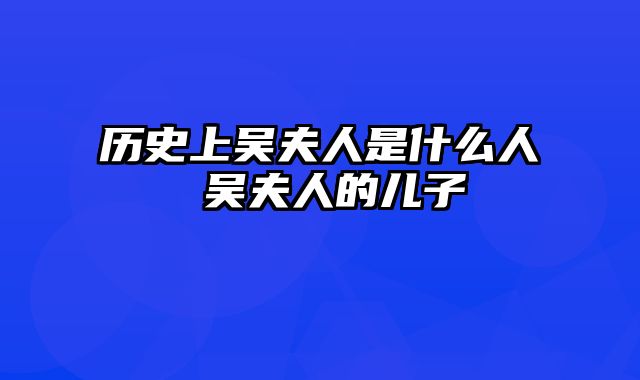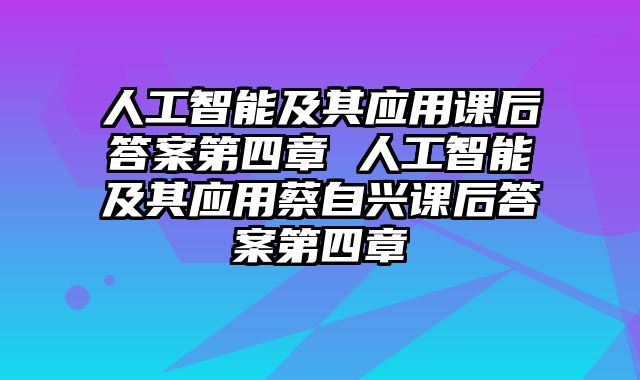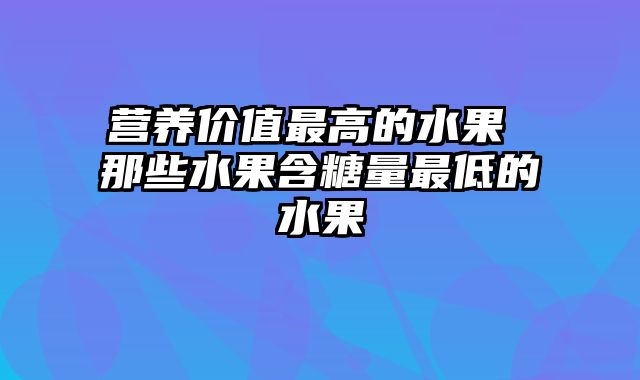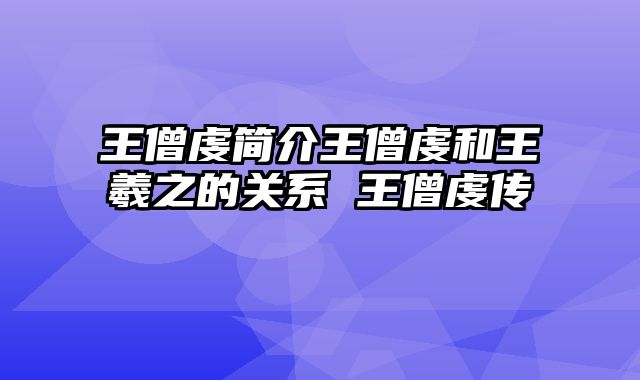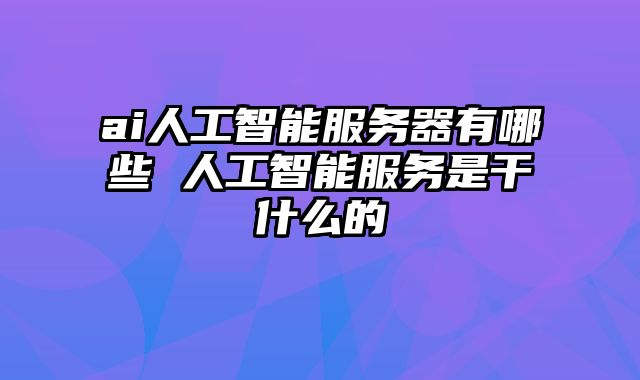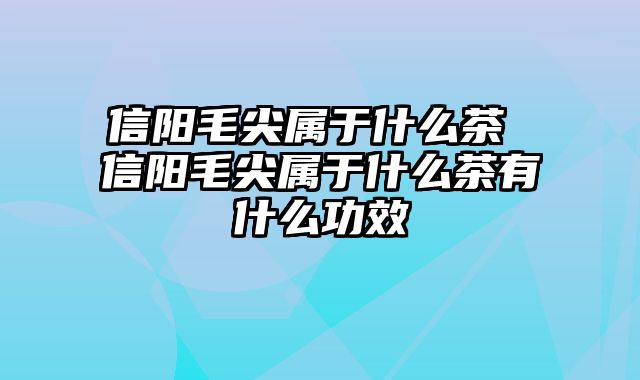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女真族作为一个重要的北方民族,先后建立了两个影响深远的王朝——金朝(1115–1234年)和清朝(1636–1912年)。这两个政权相隔数百年,但都源于东北地区的渔猎民族。那么,清朝时期的女真人与金朝时期的女真人是否属于同一个民族?这是一个涉及民族演变、语言文化传承与政治建构的复杂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历史源流、族称演变、语言文化以及政权建构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从族源上看,金朝与清朝的建立者确实具有共同的民族渊源。金朝由完颜阿骨打于12世纪初建立,其核心族群是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部落。这些部落原为靺鞨的一支,隋唐时期称“黑水靺鞨”,辽代则统称为“女真”。他们以渔猎为生,社会组织以部落联盟为主,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金朝灭亡后,女真各部逐渐分散,部分融入汉族、蒙古族或其他民族,而留在东北的残余部落实行了相对封闭的发展。
到了明朝中后期,东北地区的女真再度活跃。明廷设立建州卫、海西卫等机构管理女真诸部,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强大。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各部后,逐步整合海西女真和部分野人女真,形成新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于1616年建立后金,其孙皇太极于1636年改国号为“清”,并正式将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这一更名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历史上“女真”与金朝亡于蒙古的负面记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构建一个新的民族认同,以适应多民族帝国的统治需要。
从血统和地理分布来看,清朝的满洲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金代女真的血脉。尤其是建州女真,其先祖可追溯至金代的女真五国部、胡里改路等边远部落,这些地区在金亡后未完全汉化,保留了较多原始习俗与语言特征。清代官方文献如《满洲实录》《八旗通志》也多次强调满洲与古代女真的渊源关系,试图通过历史叙事强化政权合法性。
然而,民族并非单纯的血缘概念,而是一个集语言、文化、认同与政治建构于一体的共同体。尽管清初统治者承认与金代女真的历史联系,但他们并不简单地将自己视为金朝女真的直接延续。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本身就标志着一种新的民族意识的觉醒。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名称上,更反映在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文化实践之中。
例如,在语言方面,虽然清代满语与金代女真语同属通古斯语族,且有一定亲缘关系,但两者并不能互通。金代女真文是基于汉字改造而成的表意文字,使用范围有限,文献稀少;而清代满文则是由蒙古文创制的拼音文字,体系完整,广泛用于行政、教育与史书编纂。语言的差异说明两个时期的女真群体经历了长期的隔离与发展,文化断层明显。
在宗教信仰上,金代女真主要信奉萨满教,但也积极吸收中原佛教与儒家思想,尤其在进入中原后迅速汉化。相比之下,清朝虽同样尊崇萨满教,并将其制度化为宫廷祭祀的一部分,但更加注重藏传佛教的运用,特别是在处理蒙藏事务时,达赖、班禅的册封成为维系统治的重要手段。此外,清廷对儒家文化的接受更具选择性,强调“满洲本位”与骑射传统,防止过度汉化。
更重要的是,清朝构建的“满洲”身份是一种政治性的民族认同,而非纯粹的血缘或文化延续。八旗制度将不同来源的人群——包括女真各部、蒙古人、汉军甚至朝鲜人——纳入统一的军事—社会体系中,只要隶属满洲八旗,便可被视为“满洲人”。这种制度化的身份认定方式,使得“满洲”成为一个超越传统族裔界限的政治民族。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清朝时期的满洲人(前身为女真人)与金朝时期的女真人有着共同的族源背景,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变迁。二者之间存在文化与血缘上的延续性,但不能简单等同为“同一个民族”。金代女真是一个以部落为基础、以建立中原王朝为目标的民族集团;而清代满洲则是在明代边疆治理背景下重新整合形成的新型政治民族,具有更强的制度建构色彩。
此外,现代学术界普遍认为,“女真”作为一个民族称谓,在金亡后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直到明末才被重新激活。努尔哈赤等人借用“女真”之名,更多是出于政治象征意义,用以凝聚东北各部力量,而非真实复现金代的社会形态。正如一些学者指出:“满洲不是女真的自然延续,而是历史重构的结果。”
综上所述,清朝时期的女真人(即后来的满洲人)与金朝时期的女真人在族源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由于时间跨度大、地理环境变化、文化演进及政治目的不同,两者在民族认同、语言、制度和社会结构上已有显著差异。因此,他们应被视为同一族群谱系下的不同历史阶段,而非完全相同的民族实体。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北方民族的历史动态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