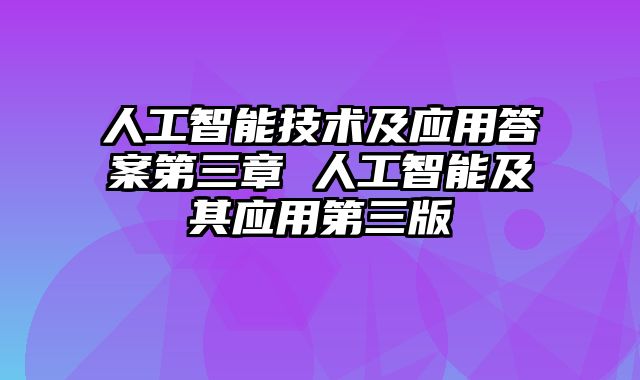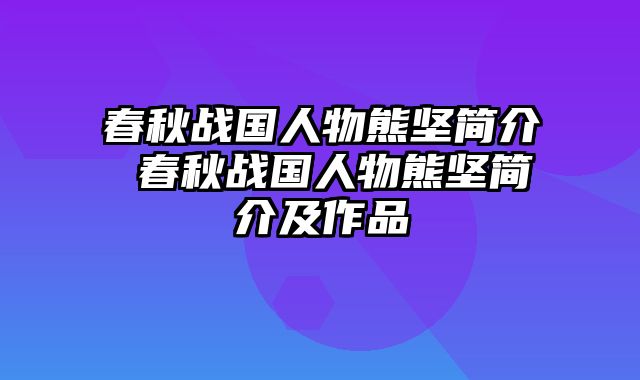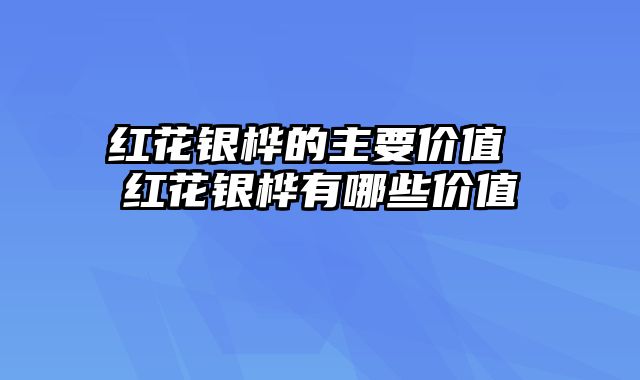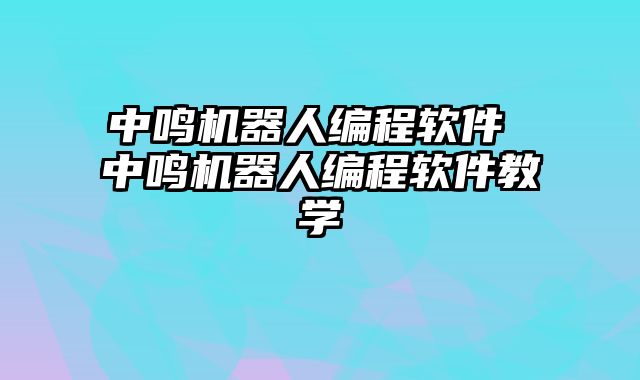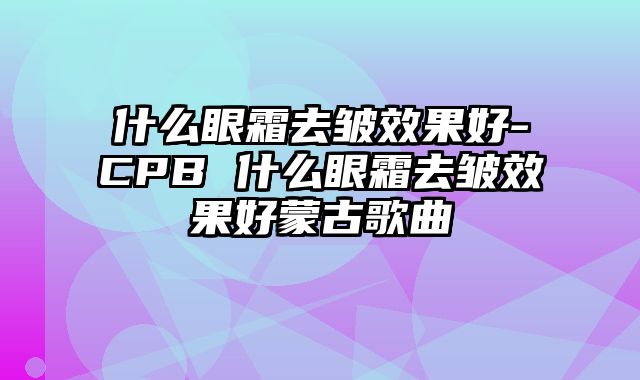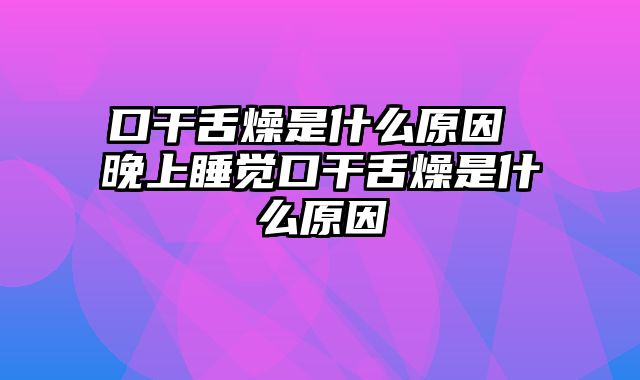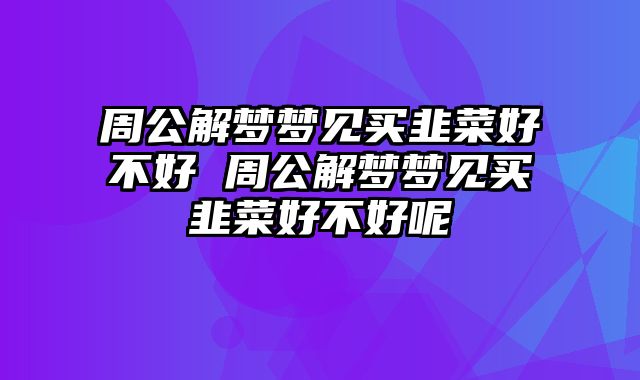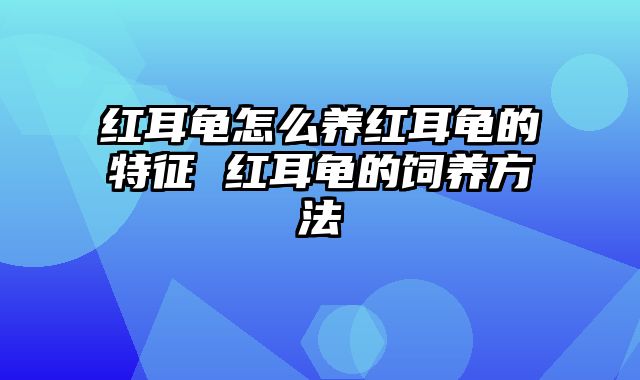雅典瘟疫爆发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当时,斯巴达军队正不断侵扰阿提卡地区,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采取了“避战固守”策略,将周边居民集中迁入雅典城墙之内,依靠坚固城防和强大的海军优势与斯巴达人周旋。然而,大量人口在短时间内涌入本就拥挤的城市,导致居住环境恶化、卫生条件急剧下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瘟疫从埃及经由海路传入比雷埃夫斯港,迅速在城内蔓延。

修昔底德对瘟疫症状的描述极为细致:患者最初出现高烧、喉咙与舌头红肿、口渴难耐,随后发展为剧烈咳嗽、呕吐、剧烈腹痛,皮肤出现溃烂与脓疱,许多人甚至在神志清醒的状态下因极度痛苦而自尽。更为可怕的是,瘟疫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照顾病患的医生和亲属往往最先被感染。据估计,在短短三年间,雅典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其中包括大量士兵、工匠与政治精英,甚至连伯里克利本人也未能幸免,于公元前429年死于这场瘟疫。
这场灾难对雅典社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首先,公共卫生体系完全崩溃。由于缺乏有效的医学知识,当时的医生无法识别病因,更谈不上治疗。人们尝试用宗教仪式、献祭神明等方式祈求庇佑,但收效甚微。死亡人数之多,使得传统的丧葬仪式无法进行,尸体被随意堆放在街道或浅埋于郊外,进一步加剧了污染与传播。
其次,道德与社会秩序瓦解。修昔底德指出,面对死亡的无常,许多人放弃了长期遵守的法律与道德准则。“既然生命如此短暂且不可预测,为何还要克制欲望?”成为普遍心态。人们开始纵欲享乐,忽视财产与家庭责任,甚至出现趁乱抢劫、侵占他人财物的现象。原本以理性、法治与公民精神著称的雅典民主制度,在瘟疫面前显得脆弱不堪。
政治层面,伯里克利之死标志着雅典温和稳健派的衰落,激进民主派如克里昂等人上台,推行更具冒险性的军事政策,导致雅典在战争中屡次做出错误决策,最终走向衰败。可以说,雅典瘟疫虽未直接终结雅典的霸权,却为其日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从现代医学视角回看,学者们对雅典瘟疫的病原体提出了多种假说,包括斑疹伤寒、麻疹、埃博拉样病毒,甚至有人推测是某种已灭绝的古代病毒。尽管确切病因至今未有定论,但其传播模式与人口密度、战争环境密切相关的特点,已被广泛认可。
此外,雅典瘟疫也深刻影响了古希腊的思想与哲学发展。在生死无常的冲击下,人们对神明的信仰产生动摇。苏格拉底虽未直接受瘟疫影响,但他所倡导的“认识你自己”“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等思想,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场灾难后人类存在意义的深刻反思。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描绘的“底比斯瘟疫”,也被视为对雅典现实的隐喻,表达了人面对命运与未知灾难时的无力感。
值得注意的是,雅典瘟疫并非孤立事件。它揭示了古代城市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时的结构性缺陷:缺乏隔离机制、医疗资源匮乏、信息传递缓慢。这些教训在后来的罗马帝国安东尼瘟疫、中世纪黑死病乃至21世纪的新冠疫情中反复重现,提醒人类文明始终面临自然力量的严峻挑战。
综上所述,雅典瘟疫不仅是一场生物学意义上的传染病爆发,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危机。它暴露了古代城邦制度的脆弱性,加速了雅典黄金时代的终结,并为后世留下了关于人性、治理与灾难应对的永恒思考。在今天全球频繁遭遇新型疫情的背景下,重访这段历史,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公元前43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席卷了古希腊最繁荣的城邦——雅典。这场被称为“雅典瘟疫”的大灾难不仅夺去了数万生命,更深刻地动摇了雅典的社会结构、政治秩序与文化信仰,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具转折意义的事件之一。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以亲历者身份详尽记录了这场瘟疫的爆发过程与社会影响,使雅典瘟疫成为西方历史上最早被系统记载的流行病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