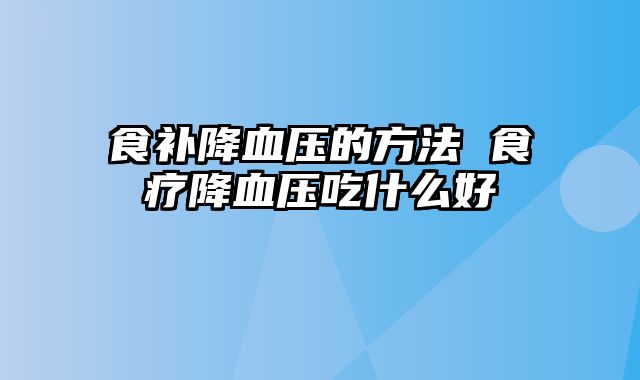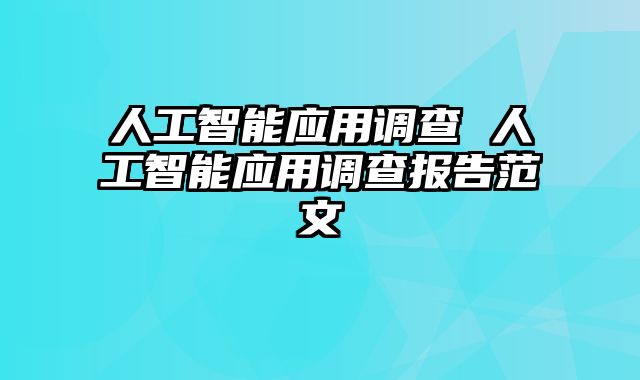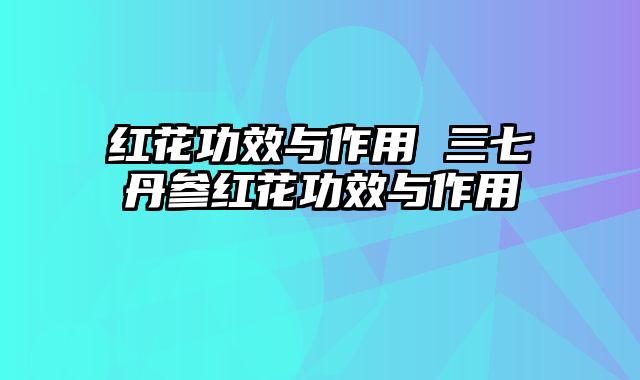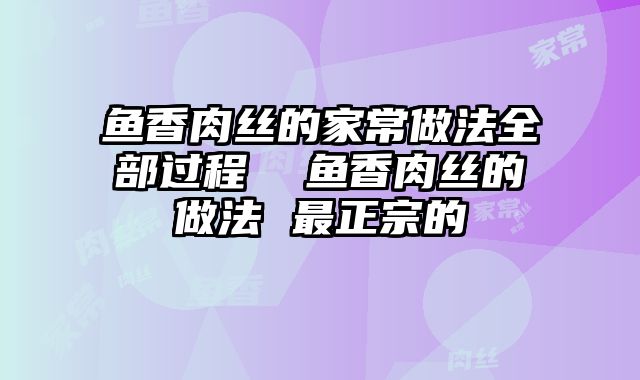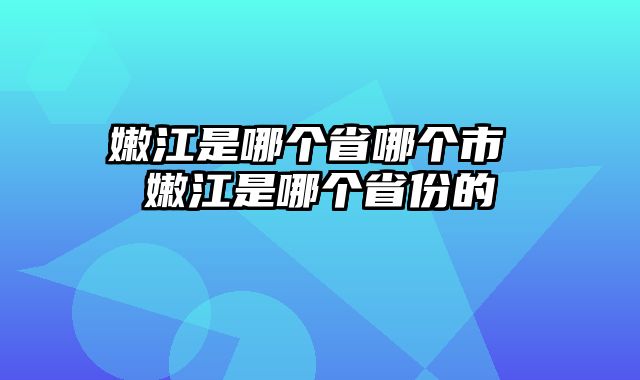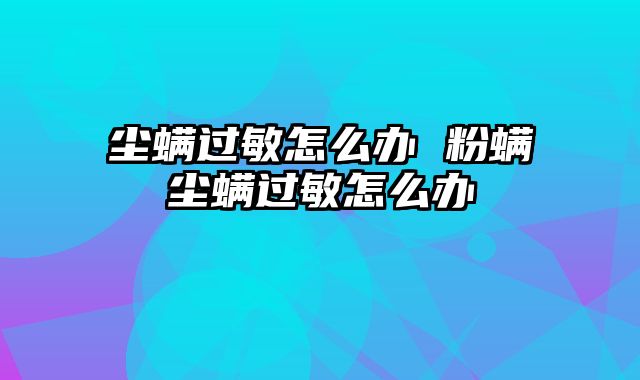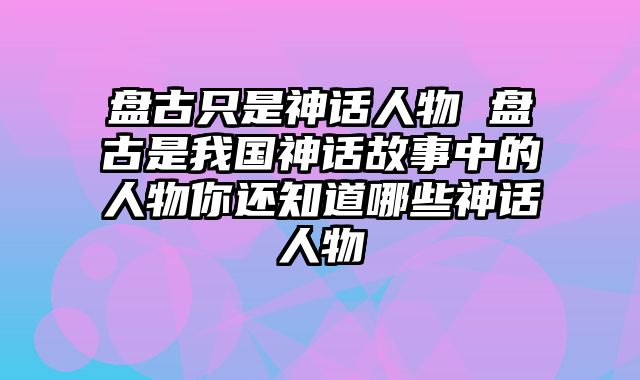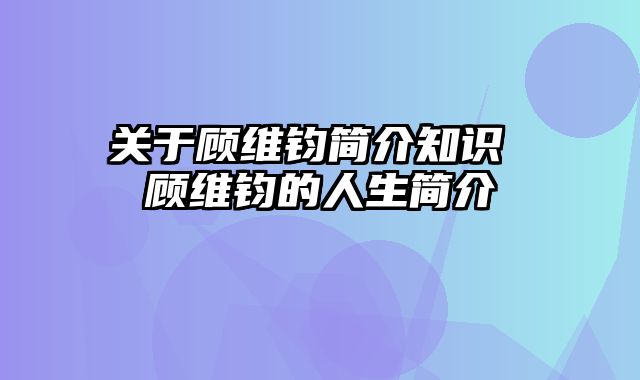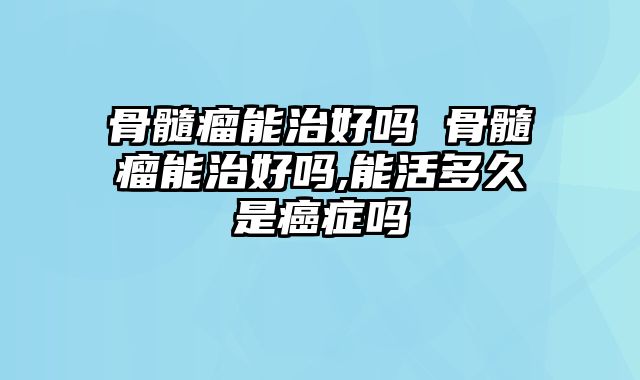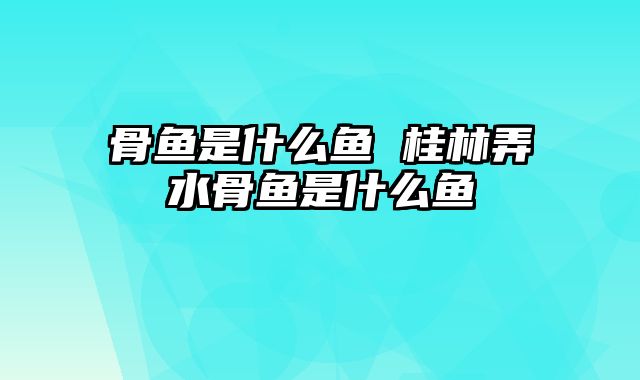在清代政治与军事体系中,八旗制度不仅是满洲政权的统治支柱,更是维系满族核心权力、分配社会资源与界定身份等级的根本性制度。自努尔哈赤于1601年初创四旗(黄、白、红、蓝),至1615年扩为八旗(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遂成集军事组织、行政单位与户籍体系于一体的复合建制。然而,八旗虽名义上“平等共治”,实则内部存在严密而固化的等级序列——其中,镶黄旗居于八旗之首,地位最为尊崇,这一排序并非偶然,而是由清初政治建构、皇权强化及制度演进共同塑造的历史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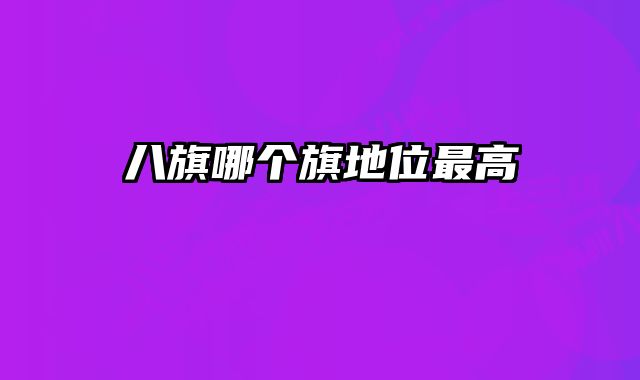
镶黄旗之所以居首,首要原因在于其与皇权的直接绑定。皇太极于天聪九年(1635年)正式确立“上三旗”体制:镶黄、正黄、正白三旗由皇帝亲统,其余五旗(正红、镶红、正蓝、镶蓝、镶白)分属诸王贝勒。而在这三旗之中,镶黄旗被明确列为“第一旗”。《大清会典》载:“凡上三旗,以镶黄为首,正黄次之,正白又次之。”其旗主历来由皇帝本人兼任,不授宗室王公;旗内佐领(牛录)多由皇帝亲选亲信包衣、功臣子弟或归附重臣充任,如康熙朝名臣明珠、乾隆朝大学士傅恒,均出身镶黄旗包衣世家。更关键的是,镶黄旗承担着最核心的宫廷护卫职能——侍卫处所辖一等侍卫、御前侍卫、乾清门侍卫,九成以上出自镶黄、正黄二旗,尤以镶黄旗为最。紫禁城北门神武门、东华门及内廷要害岗哨,均由该旗精锐轮值,所谓“近御之兵,莫重于镶黄”。
其次,镶黄旗在经济与法律特权上亦具显著优势。清初圈地运动中,镶黄旗所得京畿腴田最多、位置最优,如顺义、通州、良乡等地大片沃壤皆划入其旗地范围;雍正朝清查旗地时,镶黄旗占地规模仍居八旗之冠。在司法领域,《大清律例》明文规定:“上三旗人犯,必由内务府会同刑部审拟;若镶黄旗佐领下人涉重案,须皇帝特旨方得拘讯。”这使其成员实际享有超越普通旗人的司法豁免权。此外,科举入仕、官缺补授亦优先倾斜:清代文官“满缺”中,镶黄旗出身者占内阁学士、六部侍郎、都统等要职比例长期超三成;武职方面,健锐营、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等精锐部队的统领多由镶黄旗都统兼摄。
值得注意的是,镶黄旗的崇高地位并非静态固化,而是在清前中期持续强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短暂将正白旗升入上三旗,取代镶白旗,但镶黄旗序位始终未动;康熙平定三藩后,将原属吴三桂麾下部分汉军精锐编入镶黄旗汉军,既扩充实力,更凸显其“承天受命”的象征意义;至乾隆朝,更颁《八旗通志》,系统追述镶黄旗“肇基天命,翊戴太祖,翼卫圣躬,世笃忠贞”,将其历史叙事纳入王朝正统谱系核心。这种制度性尊崇也深刻影响社会认知:清代笔记《啸亭杂录》记,“京师谚曰:‘镶黄旗的狗,咬人不许躲’”,虽含戏谑,却折射出其实际权势之盛。
当然,需避免简单化理解——地位最高不等于实力最强。清中后期,正红旗、正蓝旗因长期驻防江南、闽粤,掌控盐政、海关、漕运等实利部门,经济影响力反超镶黄旗;而晚清湘淮军崛起后,八旗整体军事效能衰减,镶黄旗亦难挽颓势。但就制度设计、法理地位、礼仪规格与皇室信任度而言,镶黄旗作为“天子亲军之首、满洲根本之枢”,其至尊地位贯穿整个清代,从未动摇。它既是满洲贵族政治的缩影,也是清代“首崇满洲”国策最凝练的符号表达。今日北京东城区仍有“镶黄旗胡同”遗存,而故宫档案中数以万计的镶黄旗奏折、户籍册与俸饷单,仍在无声印证那段以颜色标识权力秩序的历史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