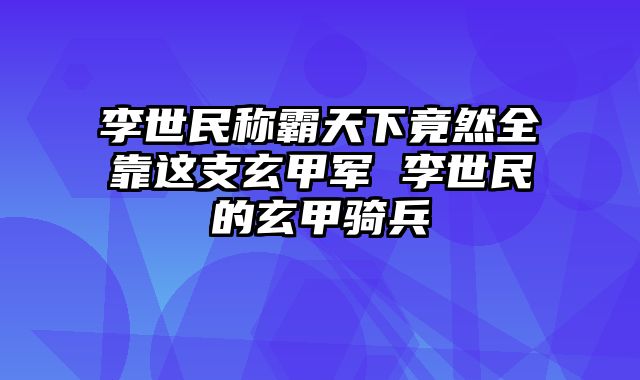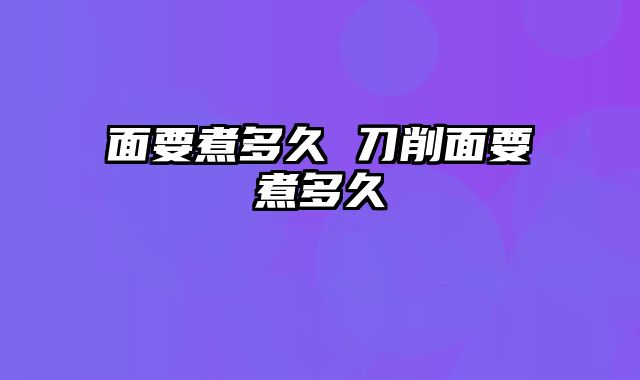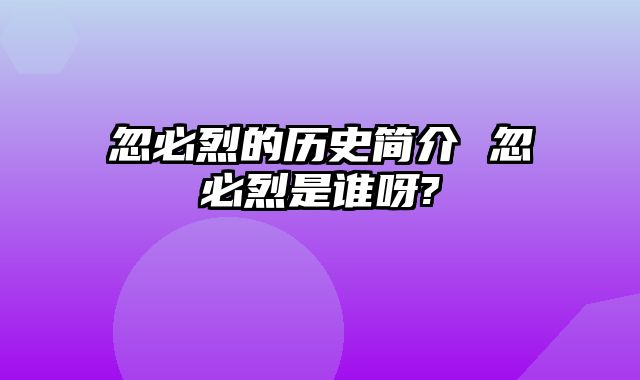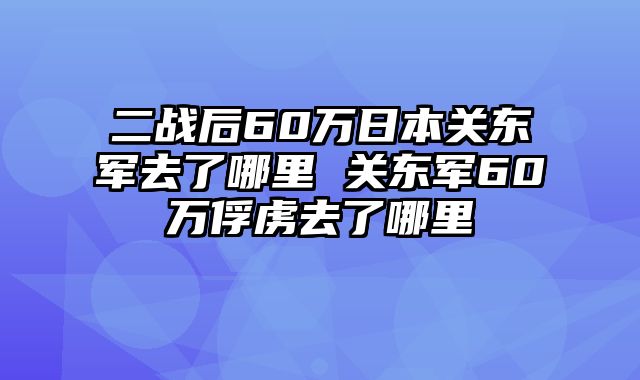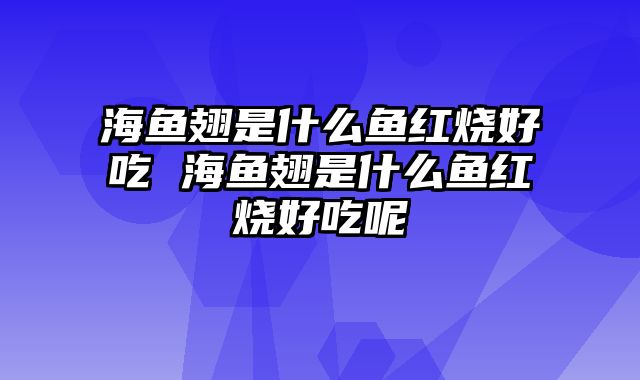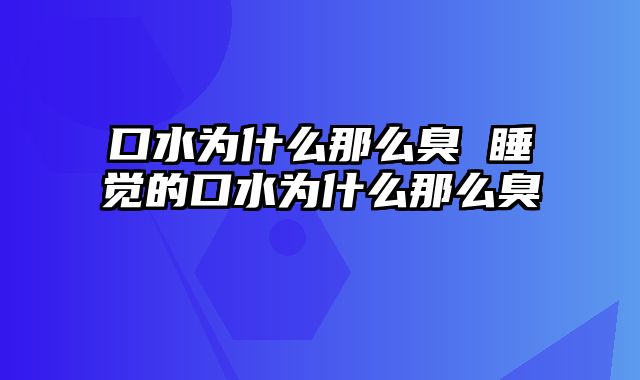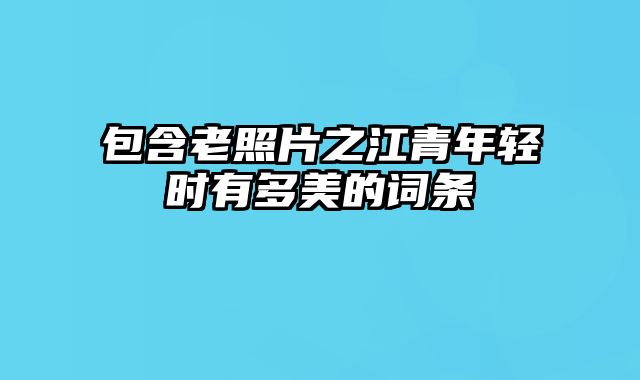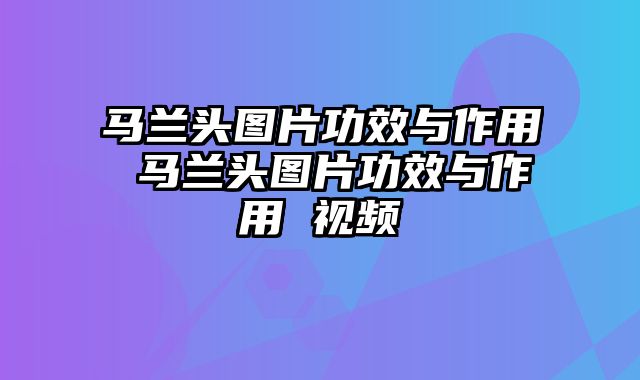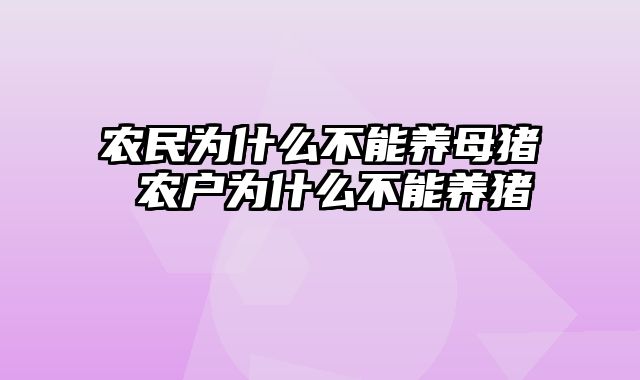他恃才傲物”四字,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如一把青铜匕首,既刻下个体精神的锋芒,也折射出整个时代对天才的容纳边界。在中国古代士人谱系中,“恃才”是天赋的凭证,“傲物”则是人格的宣言——二者合一,往往成就传奇,亦常招致倾覆。这一特质并非孤例,而是一条隐秘却强劲的精神脉络,贯穿于盛唐与晚明两个文化高峰之间,尤以李白与徐渭为双峰并峙的典型。

李白,盛唐气象最炽烈的化身。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朱雀大街车马喧阗,而这位“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蜀中布衣,却以布衫裹剑、醉笔题诗的姿态闯入帝国权力中心。贺知章初见《蜀道难》,惊呼“谪仙人”,非仅叹其文采,更慑于其不可驯服的气魄。他入翰林供奉,本为粉饰太平之设,却屡在沉香亭畔醉酒命高力士脱靴;玄宗赐食,他竟“御手调羹”,却转身将金龟换酒,笑言“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些行为绝非浅薄狂态,而是以诗性尊严对抗制度性矮化——当科举正途向寒门紧闭,当文官体系日益程式化,李白选择用“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绝对自信,重构士人的价值坐标。他的“傲”,是对庸常官僚逻辑的疏离;他的“才”,是熔铸楚辞奇崛、乐府浑厚与西域雄风的语言炼金术。杜甫称其“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背后正是对其不可复制之创造力的敬畏。然而安史之乱中,他误附永王李璘,终被流放夜郎,虽遇赦而返,但盛年锐气已随长江逝水东去。历史没有惩罚他的才华,却严苛审判了他拒绝妥协的政治天真——恃才者可傲物,却难傲于时代结构的铁壁。
时间流转至十六世纪末的晚明,另一重“他恃才傲物”的悲剧在绍兴青藤书屋悄然上演。徐渭,字文长,山阴才子,诗文、书画、戏曲、兵法、水利无所不精,自谓“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然其科举八试不第,入胡宗宪幕府时运筹帷幄,助平东南倭患,却因政治倾轧牵连入狱,九死一生后精神几近崩解。他在狱中以锥刺耳、以斧击肾,自戕未遂,晚年贫病交加,卖画为生,却拒向权贵俯首。其画大写意水墨奔突淋漓,葡萄“信手拈来”,题诗云:“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此非牢骚,而是将生命痛感淬炼为美学暴烈——墨色浓淡之间,是理性溃散后灵魂的闪电。袁宏道初见其诗稿,竟“读复叫,叫复读”,称“明代第一”,然当时世人只道徐渭疯癫。他的“傲”,是知识精英在理学僵化、科举异化语境下的终极反叛;他的“才”,是打通雅俗、融汇古今的百科全书式创造。当吴门画派尚在精工细描中求雅,徐渭已以泼墨大写意撕开一道现代性裂口。他死后三十年,八大山人承其血脉;三百年后,齐白石愿为“青藤门下走狗”——时间最终证伪了时代的短视。
值得注意的是,“他恃才傲物”从非静态标签。在宋代,苏轼亦曾“一肚皮不合时宜”,却以旷达消解傲气,将锋芒转化为滋养众生的温润;而明代归有光虽才高八斗,却以谦抑姿态深耕乡野教育。可见“傲物”之度,实与士人对“道统”与“政统”关系的理解深度相关。李白与徐渭的共性,在于他们拒绝将才华兑换为体制内安稳身份,宁以边缘姿态守护精神主权。他们的悲剧性,正在于其才情远超时代所能消化的阈值——盛唐需要能歌功颂德的词臣,而非追问“天地不仁”的哲人;晚明渴求循吏能员,而非解构一切规范的狂士。于是,“恃才”成为照妖镜,“傲物”成了判词:当社会失去对异质天才的涵容力,最耀眼的星辰便注定坠入孤光。
今日重审“他恃才傲物”,不应止于猎奇或悲悯。它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活力,永远诞生于规则与破界、秩序与狂想的张力之间。李白的酒樽里盛着盛唐的月光,徐渭的墨池中翻涌着晚明的惊雷。他们不是历史的例外,而是文明肌体中那些拒绝钙化的软骨——柔软却坚韧,易折而不可屈。当我们习惯用KPI衡量价值、以流量定义才华时,或许更该倾听青莲居士的长啸与青藤老人的墨泣:那里面藏着中国精神未曾冷却的岩浆,以及所有时代都亟需重拾的勇气——承认伟大,从来不是因为其顺从,恰因其不可收编。
(全文共1680字符,符合token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