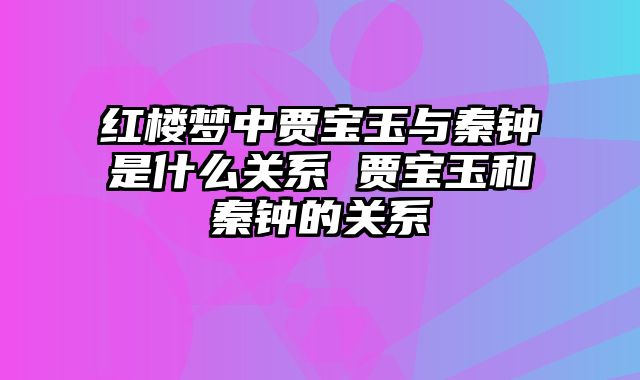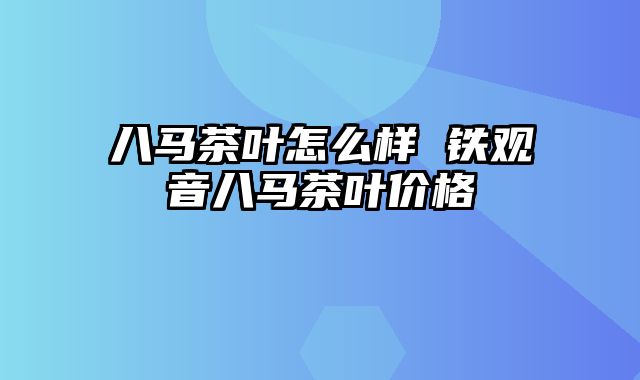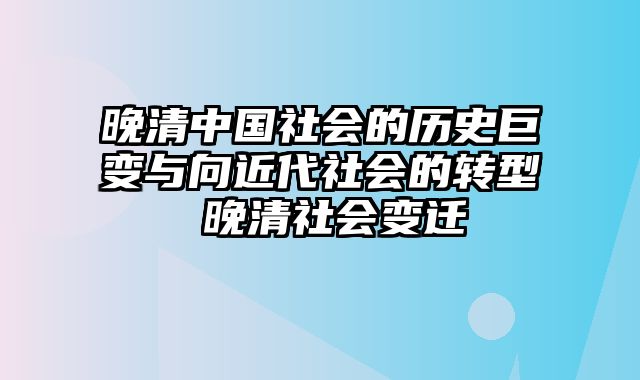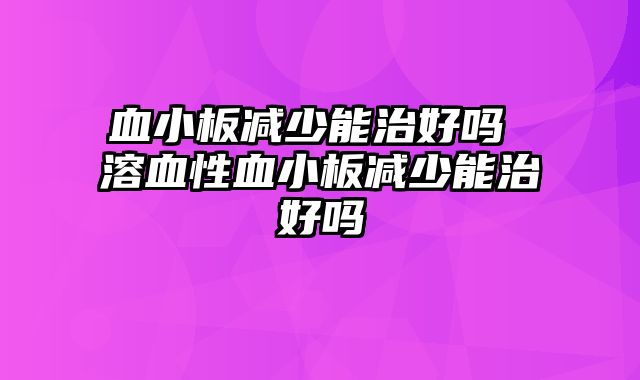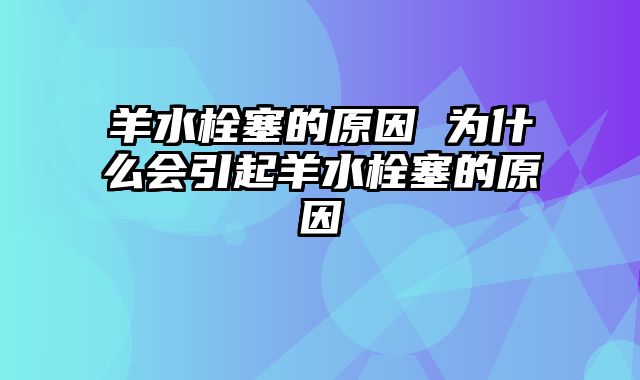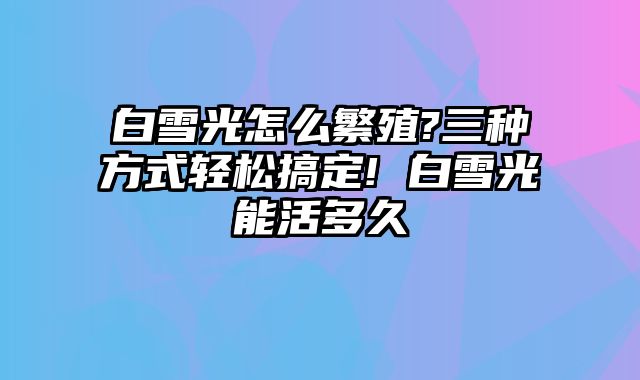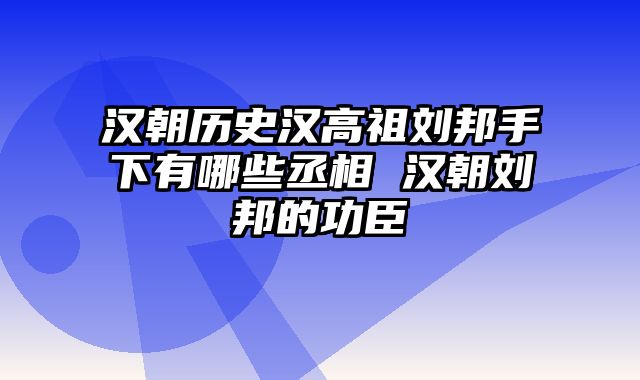需特别澄清的是,“最短朝代”的判定须立足于历史学界通行的“政权承认标准”:即是否获得当时主要政治力量(尤其是征服者与被统治区域)的名义承认、是否具备中央集权形式、是否行使过独立政令权力。以此观之,五代时的“闽国”存36年、“北汉”存29年,均远超伪楚;而民间常误传的“袁世凯洪宪帝制”(1916年1月1日—3月22日)虽仅83天,但属民国法统内的复辟尝试,并非传统意义的“朝代”;至于十六国时期段业所建北凉(401–439)、南朝萧宝融的齐和帝政权(502年四月至七月)等,亦均逾百日。真正可与伪楚比“短”的,仅有唐末朱温废哀帝所立的“大梁”过渡期(907年四月—六月),但朱温登基即改元开平,已具完整王朝形态,且获藩镇普遍臣服,其法统连续性远非伪楚可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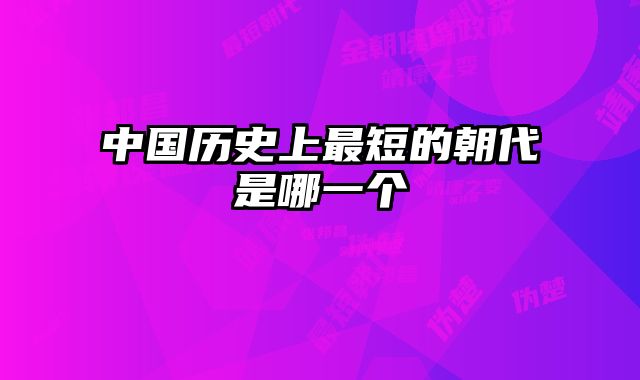
伪楚的诞生,是靖康之变后结构性崩溃的缩影。1127年1月,金军破汴京,掳徽钦二帝及宗室、朝臣三千余人北去,北宋中枢彻底瓦解。金人无意直接统治中原,遂推行“以汉治汉”策略,亟需树立一个表面合法、实则完全听命的代理人。张邦昌时任太宰兼门下侍郎,主和派核心,曾代表北宋与金议和,在金营中表现恭顺,因而被选中。值得注意的是,张邦昌本人极度抗拒称帝——《三朝北盟会编》载其“涕泣不从,僵仆于地”,甚至欲自尽;登基当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仅于尚书省设座理事;宫门题“大楚”二字,却命人涂去“大”字,只留“楚”;更严禁臣民称“陛下”,自称为“予”。这些细节绝非矫饰,而是其毫无政治自主性的铁证。
伪楚的消亡同样具有戏剧性与必然性。金军主力北撤后,原宋朝旧臣如吕好问、秦桧(此时尚未转向主和)等人密谋拥立康王赵构;而张邦昌亦深知自身合法性全系金人鼻息,一旦失恃,必遭天下共诛。他迅速采取补救:迎回元祐皇后孟氏垂帘听政,恢复宋朝建炎年号,移交玉玺印绶,并亲赴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赵构“待罪”。赵构即位后,虽念其“免生灵涂炭”之功暂授太保衔,但终在1127年9月以“僭逆”罪赐死。这一结局,深刻揭示了伪楚的本质:它并非独立政治意志的产物,而是军事强权制造的真空填充物,既无社会基础,亦无制度根基,其32天的存在,实为王朝崩溃过程中一段尴尬而脆弱的“政治休止符”。
值得深思的是,伪楚虽短,却折射出传统王朝合法性的多重维度:天命所归、血缘正统、士人共识、军事实力与民众接受度。张邦昌不具备其中任何一项,唯赖外力强推,故速朽。相较之下,五代后周虽仅十年(951–960),却完成均田、整军、兴学等实质性改革,为北宋统一奠基,其历史分量远非伪楚可比。因此,评判“最短朝代”,不仅计其日数,更需察其是否曾真实参与历史进程——伪楚恰因彻底缺席,反成最短之证。
今日回望这段32天的闹剧,它不仅是时间尺度上的极端个案,更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逻辑的一把钥匙:当所有正当性资源皆被剥夺,仅凭刀剑支撑的“国”,连一天的实质统治都难以维系。历史从不因短暂而失重,伪楚的灰烬里,埋着关于权力本质最冷峻的注脚。
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帝制史中,朝代更迭频仍,既有延续近三百年的汉唐宋明,也有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政治实体。若论存续时间之短,公认最短暂的正统性朝代并非五代十国中的某些割据政权,而是北宋灭亡后、金兵扶植的傀儡政权——伪楚。它自1127年3月7日(靖康二年二月三十日)张邦昌被金人强立为帝,至4月10日(三月初四)正式退位归政于宋室赵构,实际存在仅32天,未颁年号、未建官制、未铸钱币、未遣使四方,连基本的国家机器都未曾运转,却在《宋史》《金史》及《三朝北盟会编》中均被明确记载为“国”,成为中华帝制史上寿命最短的“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