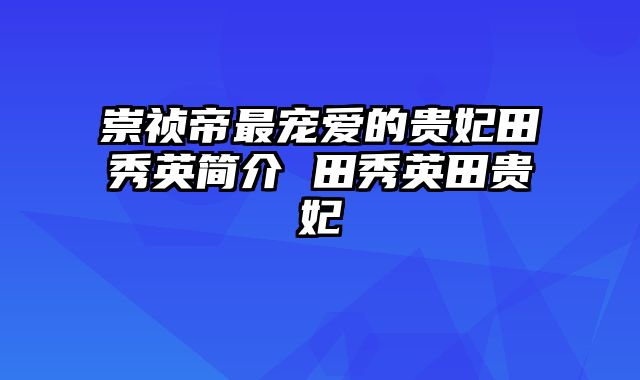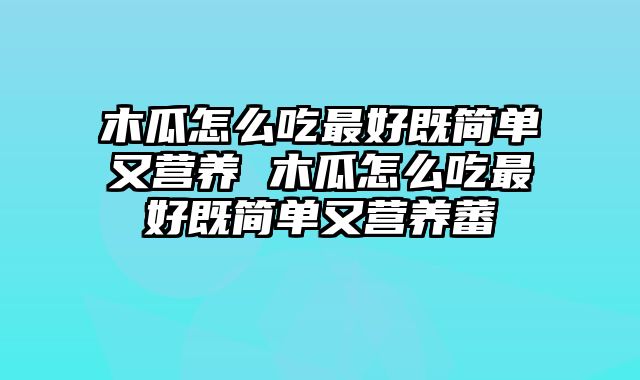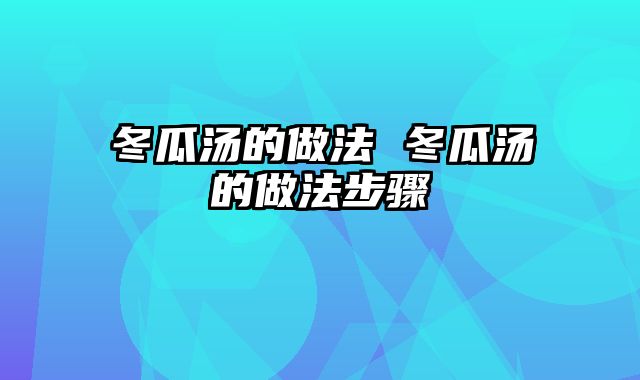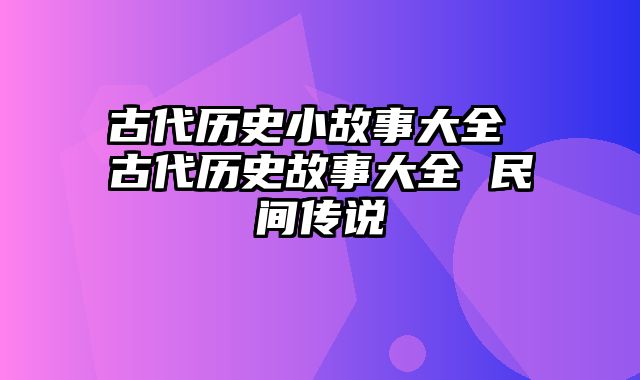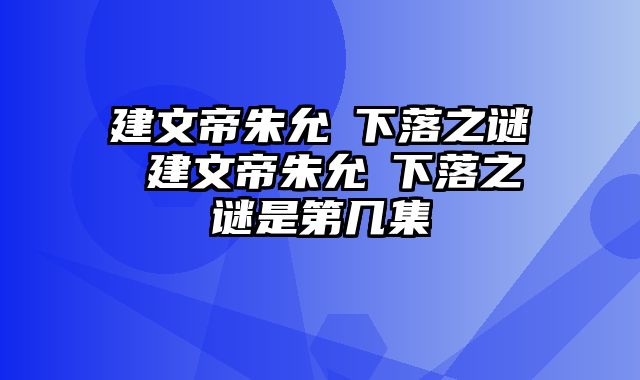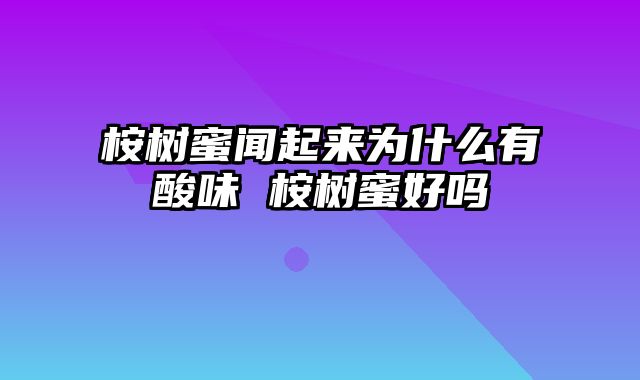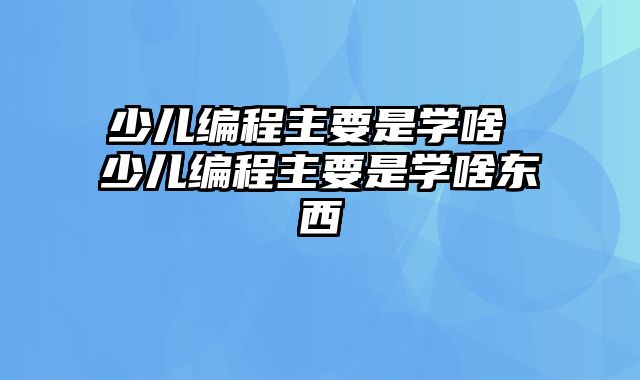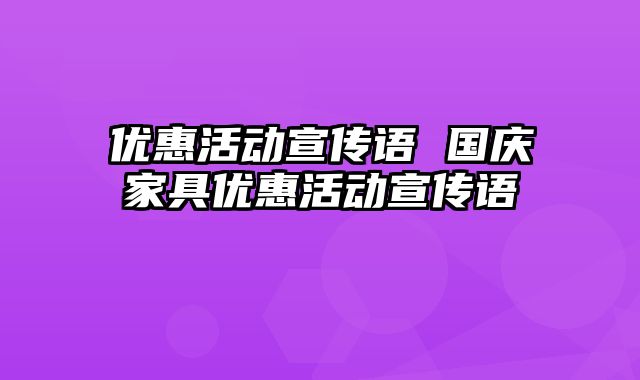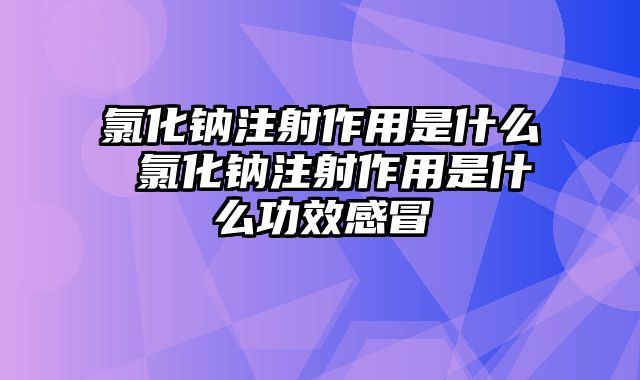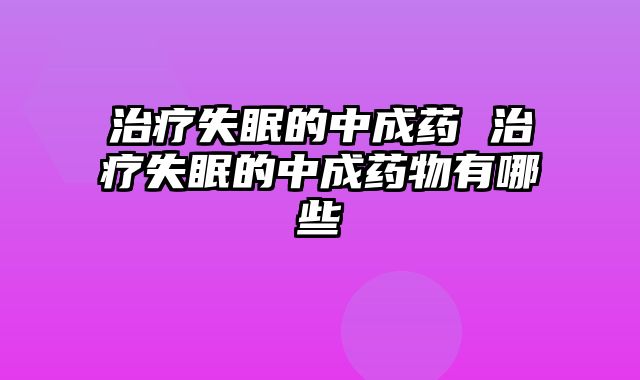首先,从原始佛典文本出发,《地藏菩萨本愿经》(唐·实叉难陀译)通篇未以生理性别定义地藏菩萨。经中称其“威神誓愿不可思议”,强调其“分身百千万亿,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所化现之身皆为度生方便。值得注意的是,“菩萨”一词在梵语中为bodhisattva,属中性名词,无语法性别;汉译虽用“他”字代指,但此乃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历史惯用,并非特指男性。早期印度佛教艺术中,如阿旃陀石窟第17窟壁画及犍陀罗浮雕所见地藏形象,多呈王子装束——头戴宝冠、身披天衣、璎珞庄严,面容清俊而无胡须,体态修长柔和,兼具勇毅与慈悲气质。此类造型源于“转轮圣王”与“大士”(mahāsattva)的理想人格范式,本质是超越世俗性别的精神圆满者之象征。

其次,汉地造像传统的性别呈现具有高度语境化特征。唐代以前,地藏多作比丘形,光头、着袈裟、持锡杖与宝珠,明确体现其“出家僧相”身份——而依律制,比丘为男性受具足戒者,故此阶段形象确以男性僧侣为蓝本。但需警惕的是:僧相是角色示现,非本体定性。正如《维摩诘经》明言:“佛身即法身,非男非女,亦男亦女。”地藏在《十轮经》中自述:“我今现作沙门之像,为欲成熟诸有情故。”可见其比丘相是应机教化的权巧示现,而非对其法身本质的限定。
至宋元以降,地藏形象发生显著流变。尤其在江南地区水陆画与民间宝卷中,出现“金乔觉化身”与“道明、闵公侍立”组合,地藏面容渐趋圆润慈和,衣饰更趋华美,部分造像甚至略带母性温润感。明代《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将金乔觉描述为“新罗国王子,二十四岁祝发,携白犬航海来华”,强化其历史人物属性;而清代以来的通俗文学与目连戏中,地藏常被赋予“幽冥教主”“慈母护婴”等复合职能,其救拔婴灵、安抚亡魂的叙事,无形中吸纳了民间对女性守护神的期待心理。这种文化层累并未改变其经典定位,却使大众感知趋向柔化,甚至误读为“女性菩萨”。
再考语言翻译层面。“地藏”梵名Kṣitigarbha,kṣiti意为“大地”,garbha意为“胎藏、含藏、宝藏”,合指“如大地般含藏一切功德种子,能出生万善”。此名本身无性别指向。玄奘译《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称其“安忍不动,犹如大地”,突出其德性特质而非形貌特征。而“王”字加称(地藏王菩萨),系汉地尊称习惯,类同“观音王”“文殊王”,属敬语后缀,非政治性封号,更不暗示性别。
尤为重要的是佛教根本义理立场。《大般若经》《金刚经》反复申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菩萨于法,应无所住”。性别概念属于“假名施设”,在胜义谛中本不可得。《楞严经》更直言:“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菩萨可化现天、人、阿修罗乃至畜生、饿鬼之形,男相女相皆为度生方便。因此,执着于地藏是男是女,恰与佛法破执宗旨相违。近代高僧印光大师曾开示:“菩萨随缘示现,岂拘男女?若必执相而求,则失其本矣。”
当然,当代性别研究视角亦提供新思。学者如Rita M. Gross指出,佛教传统中虽有“女身不能成佛”等历史表述(见《首楞严经》争议段落),但大乘经典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已借龙女八岁成佛公案,彻底消解性别障碍。地藏信仰在东亚女性信众中尤为普及,因其救度亡亲、超荐堕胎婴灵等功能,契合传统女性在家庭祭祀与生死关怀中的核心角色。这种信仰实践中的“柔性共鸣”,是文化适应的结果,而非教义设定。
综上,地藏王菩萨在经典中无固定生理性别,在造像中依时代与功能需要呈现多元样貌,其本质是超越二元对立的法身悲智之化现。与其追问“是男是女”,不如体认其“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愿力深度与“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担当广度。真正的理解,始于放下概念分别,归于对大愿精神的虔诚践行。
在汉传佛教信仰体系中,地藏王菩萨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大愿闻名于世,其形象常见于寺院地藏殿、民间超度法会及《地藏经》诵持场景中。然而,一个长期萦绕大众认知的疑问始终未被充分澄清:地藏王菩萨是男还是女?这一问题表面关乎性别指称,实则牵涉佛教义理、图像学传统、翻译史、本土化过程及宗教符号的象征逻辑。要准确回答,须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从经典依据、造像演变、梵汉译释与文化接受四个维度展开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