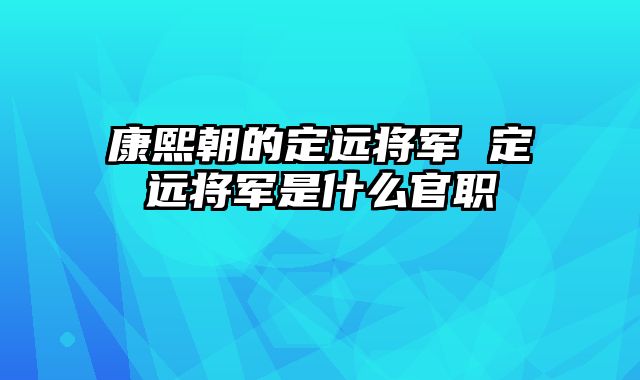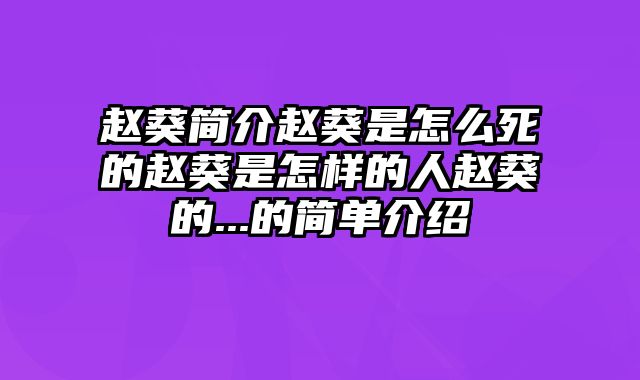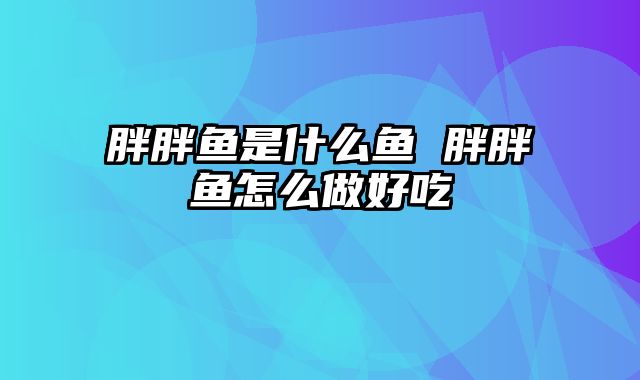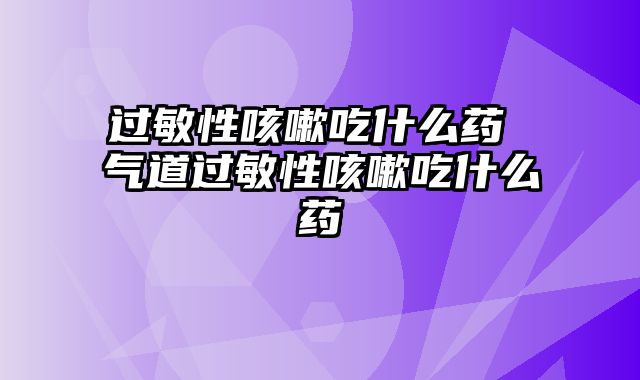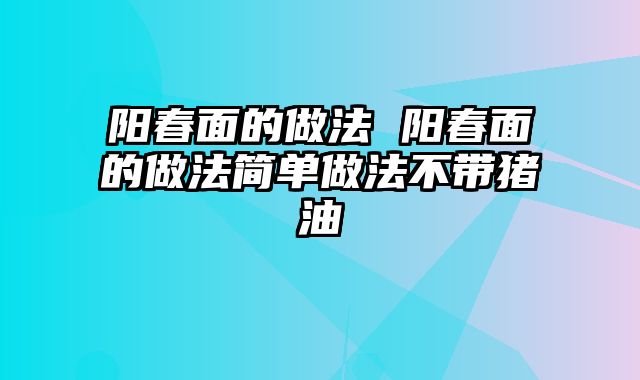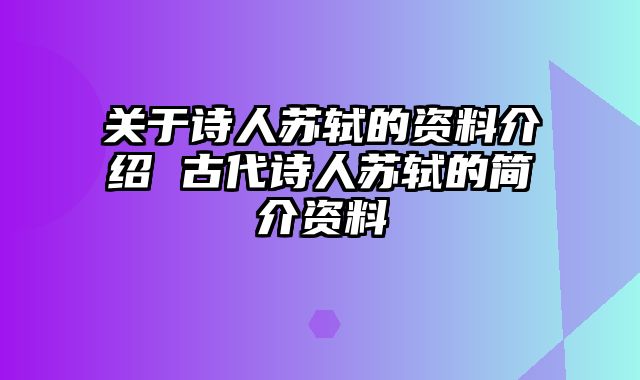从语音学角度看,叠韵之“韵”特指中古汉语的“韵部”概念。隋代陆法言《切韵》将汉字按韵母系统分为193韵(后增补为206韵),每一韵部内收字须具备相同的韵腹、韵尾及声调。例如“东”“同”“隆”“风”均属《广韵》“东韵”,其韵母为[uŋ](平声),声调一致,即构成严格意义的叠韵。值得注意的是,叠韵不涉声母,亦不苛求介音完全相同——如“江”(*kɔŋ)与“邦”(*pɔŋ)虽声母迥异、介音微殊,但在《切韵》体系中同属“江韵”,仍属叠韵;而“花”(*hʷæ)与“华”(*hʷa)在《广韵》分属麻韵与麻韵重纽,因等第不同、实际音值有别,反不构成叠韵。这种精密性,凸显了中古音系对“韵”的结构性定义。

叠韵在文学实践中的功能远超语音装饰。在六朝至初唐的永明体诗中,沈约等人倡“四声八病”说,“旁纽”“正纽”备受关注,而叠韵尚未成为独立修辞焦点。真正使叠韵升格为诗学范畴的,是盛唐以后近体诗格律的成熟与词体的兴起。杜甫《秋兴八首》中“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斜”(xiá)与“华”(huá)在中古属麻韵平声,构成叠韵呼应;更典型者如李贺《梦天》“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色”(sè)、“白”(bó)虽今读声调不同,然在《广韵》中同属入声陌韵,韵核[ək]一致,属严格叠韵。此类用法强化句末节奏张力,赋予诗句沉郁顿挫的听觉质感。
至宋代,叠韵更被提炼为一种高度自觉的文体实验。苏轼曾作《次韵子由题吴道子画后》,其“次韵”即要求不仅步原诗之韵部,且须使用原韵字(如原用“空”“风”“虹”,和诗亦须用此三字),此即“叠韵唱和”。黄庭坚《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更以“叠韵体”独立成篇:“平生久无客,今日独何人?滩头谁唤渡,柳外自藏春。”全诗四句末字“人”“人”“渡”“春”,表面看仅“人”“春”可通押,实则依《广韵》,“人”(jɪn)、“渡”(duoH)、“春”(tɕʰiuŋ)分属真、遇、谆三韵,并不叠韵——这正说明宋代文人已开始突破中古韵部束缚,在方言音感与诗意优先原则下重构叠韵标准,体现音韵规范向文学表达让渡的历史转向。
值得注意的是,叠韵在非诗歌领域亦具制度性意义。清代考据学家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提出“古本音”说,通过分析《诗经》中大量叠韵联绵词(如“参差”“窈窕”“辗转”),推断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与特殊韵尾,为汉语语音史重建提供关键证据。王国维《观堂集林》进一步指出:“凡叠韵之字,多为状貌情态之词”,揭示叠韵与汉语“以音表意”的原始思维密切相关——语音的重复本身即模拟事物的连续性、模糊性或动态性,如“徘徊”摹踟蹰之态,“伶仃”状孤寂之形。这种音义关联,使叠韵超越修辞技巧,成为理解汉语文化思维模式的一把钥匙。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语言学传入与国语运动推进,叠韵概念经历现代转译。章太炎《国故论衡》仍坚持中古韵部标准,而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则以“韵母相同”定义叠韵,弱化声调要求。当代学者如鲁国尧、郑张尚芳通过构拟上古音,证实《诗经》“关关雎鸠”中“关”(*kroon)、“鸠”(*ku)实为叠韵(-oon/-u属同韵摄),修正了传统“鸠”属幽部、“关”属元部的旧说。这些研究表明,叠韵不仅是古典诗律的标尺,更是汉语语音演变的活化石与跨学科研究的枢纽。
综上,“历史百科何谓叠韵”之问,答案绝非一个静态定义。它是隋唐韵书规范下的语音分类法则,是杜甫沉郁、李贺奇崛的声律载体,是苏黄唱和中的文人游戏,是段王考据里的上古密码,亦是今日语言学重建汉语史的关键坐标。当我们诵读“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苍”“霜”在《广韵》同属阳韵平声,叠韵如双璧相映,千年不散——那不只是声音的重复,而是文明记忆在时间褶皱中一次精准的共振。
叠韵,是中国传统音韵学与古典诗歌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指两个或多个字的韵母(包括主要元音、韵尾及声调)完全相同,从而在诵读中形成回环往复、谐婉绵长的语音效果。它并非现代汉语拼音意义上的简单“押韵”,而是在中古汉语音系框架下,经由《切韵》《广韵》等韵书系统规范、并在唐宋以降诗词创作实践中高度自觉运用的语言现象。理解“叠韵”,需置于汉语语音史、诗体发展史与文人审美观念史三重脉络中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