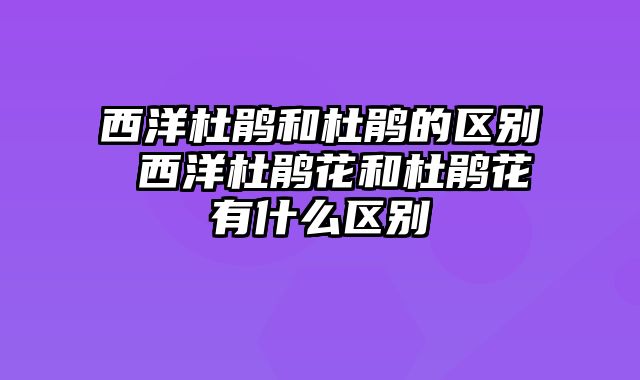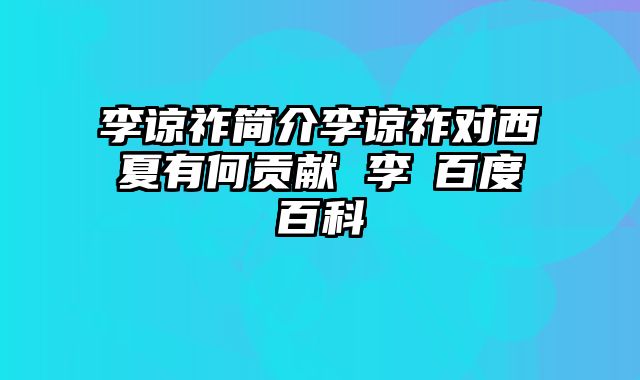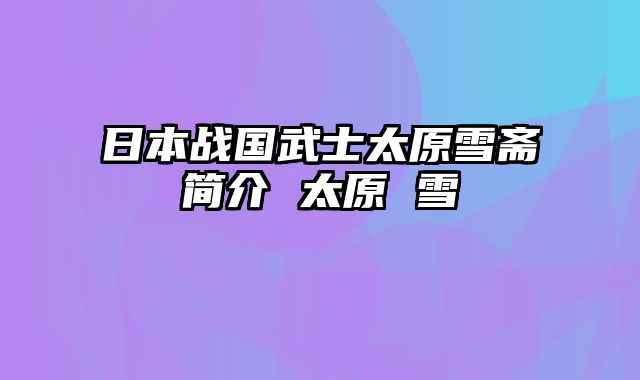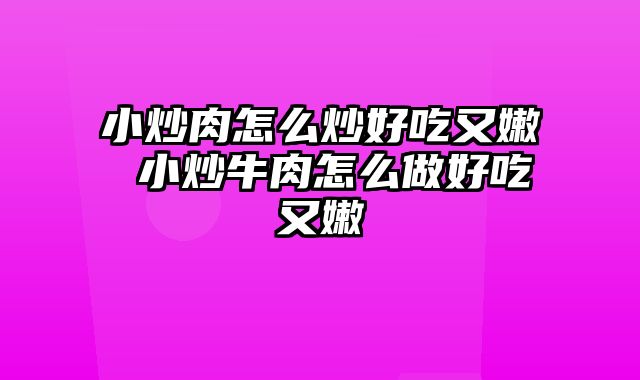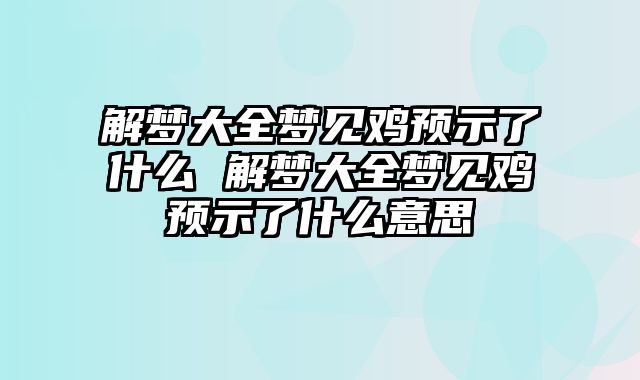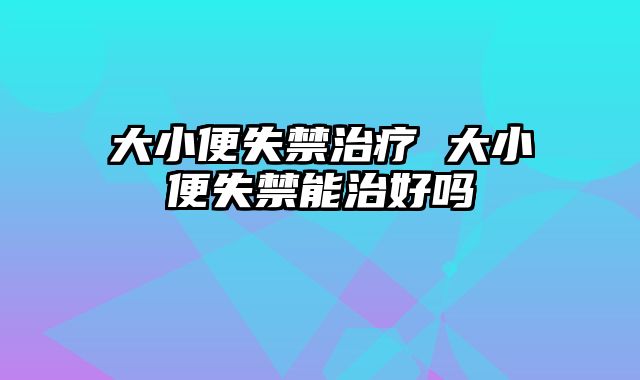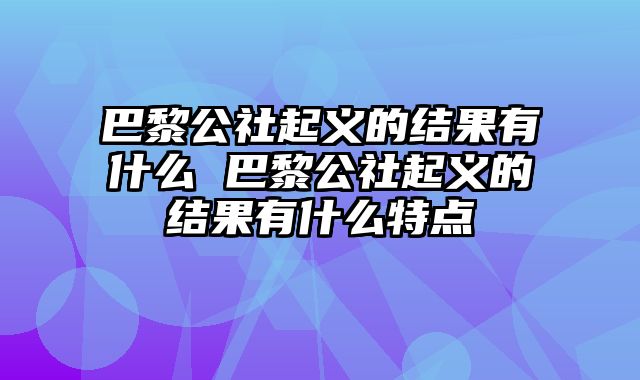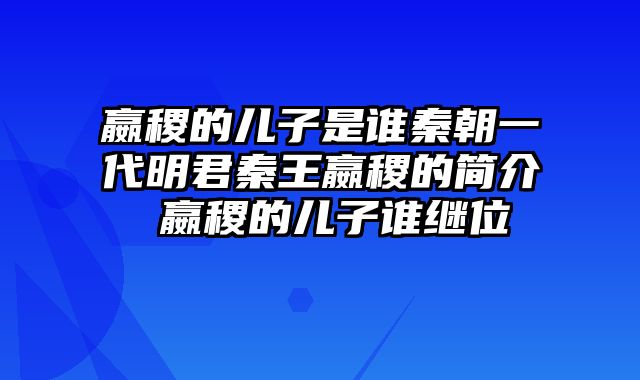第一,亡命奔涿郡(约184年)。关羽因在家乡“犯事”杀豪强而逃亡,辗转至幽州涿郡,结识刘备、张飞,三人“恩若兄弟”,于桃园结义——虽“桃园结义”属后世文学概括,但《三国志》明确记载“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体现早期政治同盟的情感基础与组织雏形。

第二,随刘备转战青徐(191–194年)。关羽参与讨伐黄巾余部、镇压黑山军、协助陶谦守徐州等战役,初显勇略。《三国志》载其“万人敌”之誉即源于此阶段实战表现,尤以在下邳突围、掩护刘备家属撤退等行动中展现卓越指挥与断后能力。
第三,建安五年降曹与白马解围(200年)。官渡之战前,刘备被曹操击溃于小沛,关羽暂归曹营。曹操厚待之,拜偏将军。当袁绍大将颜良围白马,关羽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而还,“绍诸将莫能当者”,此役直接扭转官渡战局,亦是正史唯一明确记载其单骑突阵斩将的战例,奠定其超凡武勇的历史实证。
第四,挂印封金,千里寻兄(200年)。得知刘备在袁绍处后,关羽尽封曹操所赐金银印绶,留书辞别,北上穿越曹境数郡。此举非仅忠义象征,更是对汉末士人“主从契约”的实践——效忠对象具人格性与道义性,而非单纯依附权势。
第五,镇守荆州南郡(214–219年)。刘备入川后,命关羽“董督荆州事”,总揽军政。他整饬水军、屯田积粮、修筑江陵城防,并与东吴周旋:既与鲁肃“单刀会”协商疆界,又严拒孙权联姻请求,称“虎女焉配犬子”,反映其刚直不阿的政治立场与战略清醒。
第六,襄樊之战与水淹七军(219年秋)。关羽北伐曹仁,围樊城、襄阳。时值秋雨连绵,汉水暴涨,关羽乘大船攻陷于禁七军,擒于禁、斩庞德。此役非偶然水患所致,而是其长期经营水军、熟谙汉水汛期与地形的主动战术成果,《华阳国志》称“羽乘船攻于禁等,遂没七军”,凸显其作为统帅的谋略维度。
第七,吕蒙白衣渡江与江陵失守(219年冬)。孙权采纳吕蒙密计,以商船伪装、精兵潜袭,袭取公安、南郡。关羽后方空虚、将士家属尽落敌手,军心瓦解。此事暴露其外交失衡——未能维系孙刘联盟底线,亦低估东吴战略决心,成为其军事生涯转折点。
第八,败走麦城与临沮被俘(219年十二月)。关羽弃守麦城,率十余骑西行欲入蜀,途中遭潘璋部将马忠伏击于临沮夹石。《三国志》仅记“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未提“过五关斩六将”等演义情节,其败亡本质是孤军无援、补给断绝、情报失效的系统性溃败。
第九,首级送洛阳与曹操厚葬(220年初)。孙权为嫁祸曹操,将关羽首级送至洛阳。曹操识破其计,以诸侯礼葬于洛阳城南,此为汉末罕见的敌对阵营间礼遇,侧面印证关羽在当时士林与政治话语中的崇高地位。
第十,身后追谥与历史升格(260年始)。刘禅于景耀三年追谥“壮缪侯”,虽“缪”含“名与实爽”之贬义,但宋代以降,历代帝王屡加追封:宋徽宗封“义勇武安王”,明神宗晋“三界伏魔大帝”,清乾隆钦定“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这一持续千年的神化过程,实为儒家忠义观、民间信仰、国家祀典与商业伦理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观关羽十事,其历史形象始终在“人—将—臣—神”四重维度间动态演进。他并非完美无瑕:刚而自矜、轻慢士大夫、外交短视,却正因这些真实缺陷,使其忠勇更具人性厚度。研究关羽,不仅是还原一位武将的履历,更是解码汉末社会结构、军事制度、伦理秩序与集体记忆建构机制的重要切口。他的刀锋曾劈开乱世迷雾,而他的名字,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精神谱系中不可替代的坐标。
关羽,字云长,河东解县人,东汉末年著名将领,蜀汉开国功臣,被后世尊为“武圣”。其一生贯穿汉末群雄割据至三国鼎立初期,既是真实历史中的军事统帅,也是文化史中不断被层累塑造的道德符号。梳理其可信史实,需以《三国志·关羽传》为核心依据,辅以《后汉书》《资治通鉴》等权威史料,剔除《三国演义》虚构情节干扰。以下十件关键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呈现其真实轨迹与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