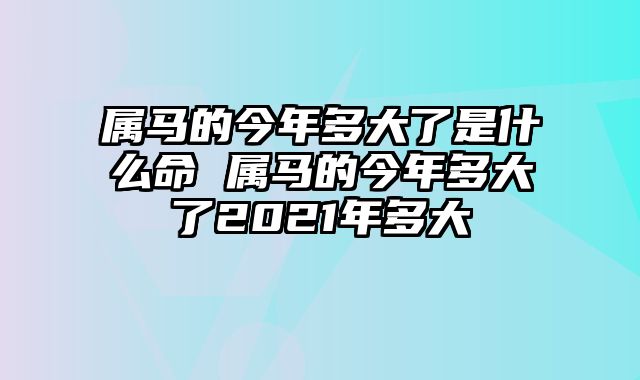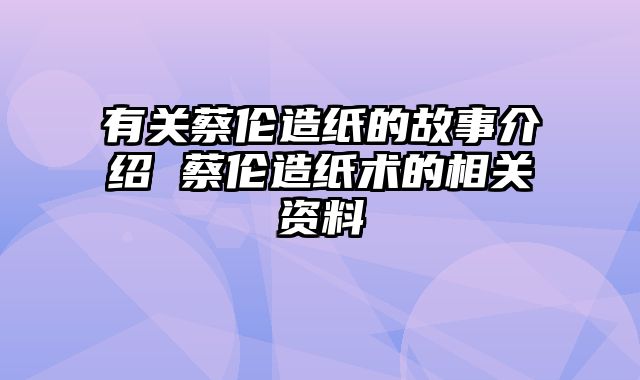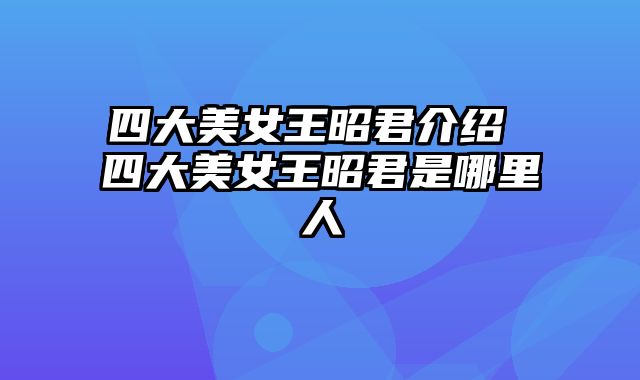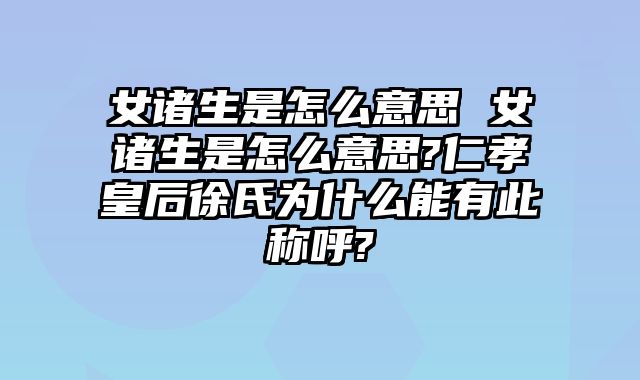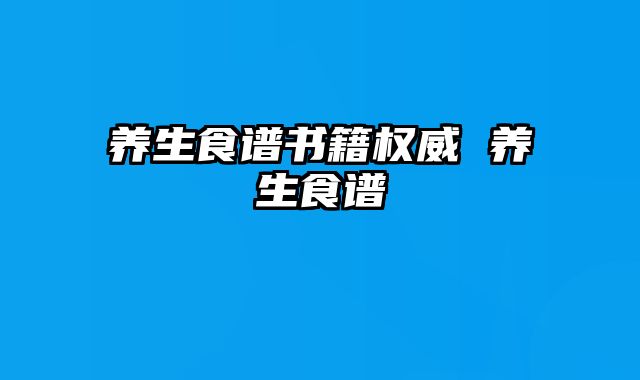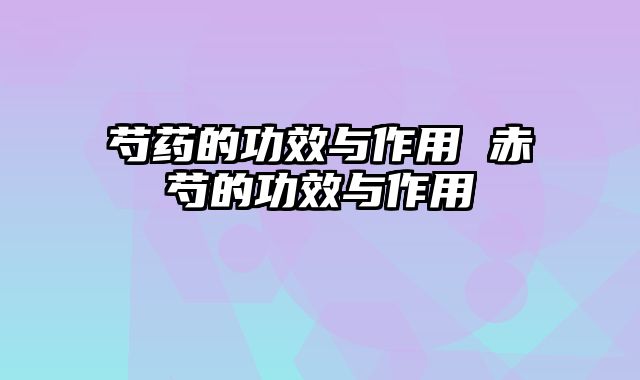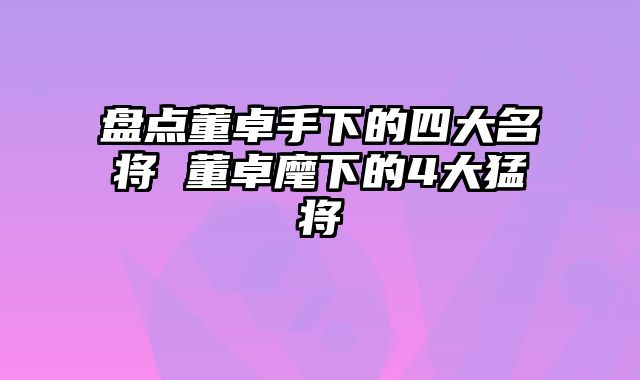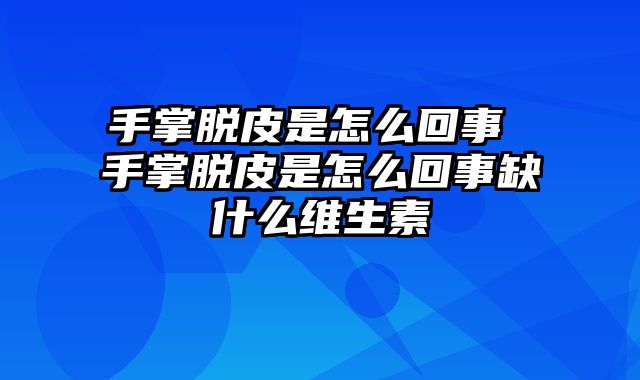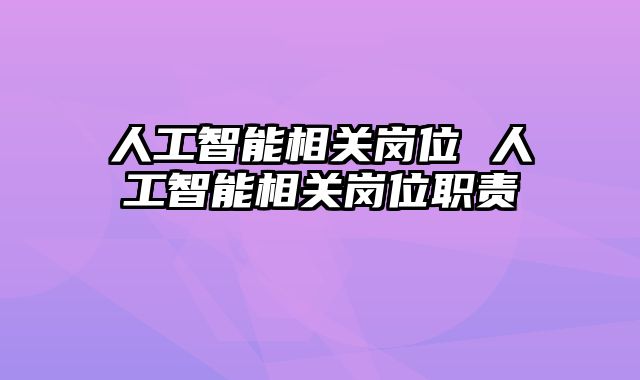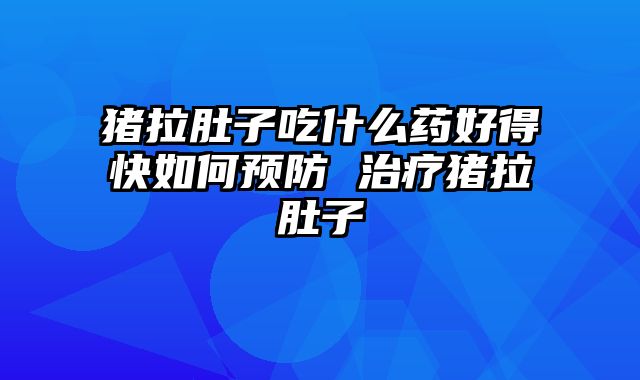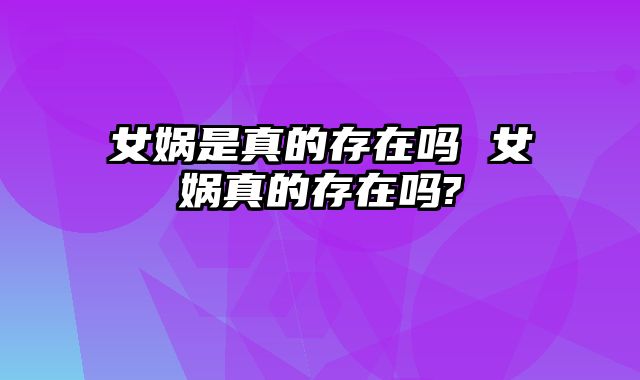东晋(317–420年)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皇权弱而士族强”的政权形态。它并非凭借武力统一或制度创新立国,而是西晋崩溃后,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北方南迁士族,在建康(今南京)拥立司马睿建立的偏安王朝。这一政权的存续,本质上依赖于皇室与顶级门阀之间脆弱而精密的政治契约——其中,王导辅政堪称东晋门阀政治成型的奠基性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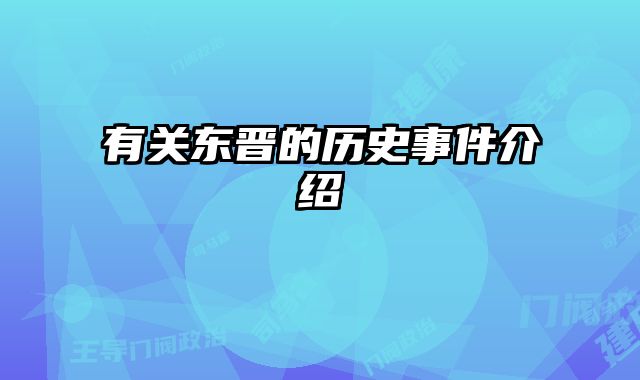
公元307年,琅琊王司马睿受命镇守建邺(后改名建康),其时江东人心未附,吴姓士族观望疏离,北来流民武装亦各自为政。真正扭转局面的是时任安东司马的王导。他不仅为司马睿规划江南立足方略,更以极富象征意义的“三月三曲水流觞”活动,邀集顾荣、贺循等吴中名士共赴新亭雅集,借礼乐仪轨消解地域隔阂;又力主“镇之以静”,对周玘等地方豪强既授官职又严控兵权,避免激化矛盾。永嘉南渡后,王导更主导设立“侨置郡县”,安置百万北来士庶,将流民编入“白籍”,保留其原籍郡望,既维系士族身份认同,又规避与土著争夺资源。这种柔性治理,使建康政权迅速获得合法性根基。
王导执政二十余年(318–339年),历仕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官至丞相、录尚书事,却始终不称“摄政”,不居相府,常于西州门听政,自称“仆射”,以谦抑姿态维系君臣表象。他深知东晋皇权不可独尊,亦不可旁落——故扶持庾亮出镇荆州以制衡王敦,又在王敦之乱(322、324年)中一面痛斥其弟悖逆,一面暗助成帝稳定中枢,最终以“王与马,共天下”八字精准概括了权力结构:琅琊王氏提供政治纲领与行政能力,司马氏提供法统符号与宗法正统,二者缺一不可。
这一格局深刻塑造了东晋政体:中枢决策多由“中书监”“录尚书事”等门阀高官主导,皇帝诏令需经门阀领袖副署方具效力;选官实行“九品中正制”的变体,上品几乎全被王、谢、庾、桓四大家族垄断;军事则形成“上游荆襄—中游江州—下游扬州”的门阀分镇体系——庾氏据荆州、桓氏继之,谢氏掌北府兵,王氏守中枢,彼此牵制又协同御外。淝水之战(383年)的胜利,表面是谢玄指挥得当,实则依赖谢氏长期经营北府兵、王珣稳定朝议、桓冲让出上游战略空间的门阀协作机制。
然而,门阀政治亦埋下结构性危机。士族重清谈轻实务,庄园经济导致赋税锐减,军功阶层(如刘牢之、刘裕)在寒门将领崛起后渐失控制力。至安帝朝,桓玄篡位(403年)暴露门阀联盟瓦解,而刘裕以寒人出身整合北府旧部,废晋建宋(420年),标志“共天下”模式终结。值得注意的是,王导之后的谢安、王彪之等人虽延续调和政策,但已无力阻止门阀内耗加剧——孝武帝试图倚重王国宝压制谢氏,反致政局崩坏;会稽王司马道子纵容亲信排挤太原王氏,加速统治集团分裂。
从制度遗产看,东晋的侨置郡县催生了南朝“黄白籍”户籍体系;其“清谈玄理”推动佛学与玄学融合,促成《肇论》《高僧传》等思想高峰;建康都城建设更奠定六朝文化地理格局,乌衣巷、朱雀桥成为士族文化的物质铭刻。今日南京城南的“王导谢安纪念馆”仍存宋代碑刻“江左风流”,所纪念的不仅是个人功业,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以士族共识替代绝对皇权的制度实验。
这段百年实践表明:门阀政治并非简单的贵族专政,而是在胡族压境、法统残缺、社会解组的极端条件下,精英集团以血缘、婚媾、学术与地缘纽带构建的替代性治理秩序。它的兴衰启示后世:任何政治结构若丧失吸纳新力量的能力,终将被更具组织效能的集团取代——刘裕的北府兵,恰是以军事效率重写士族游戏规则的终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