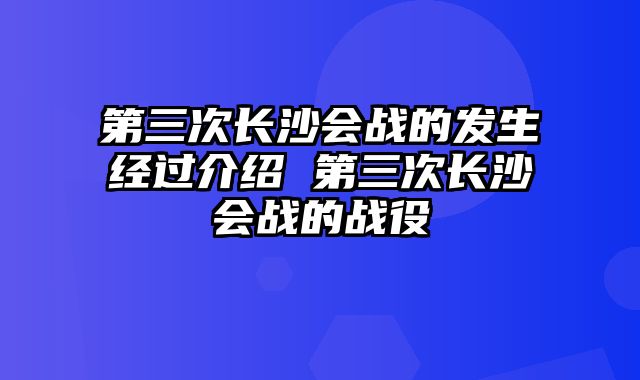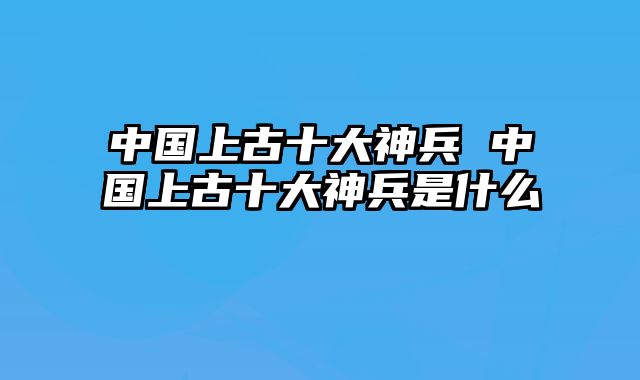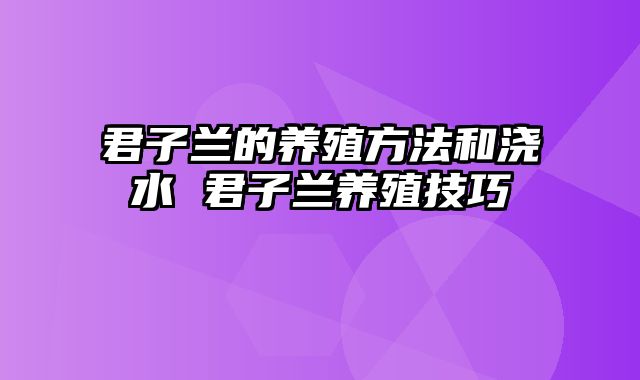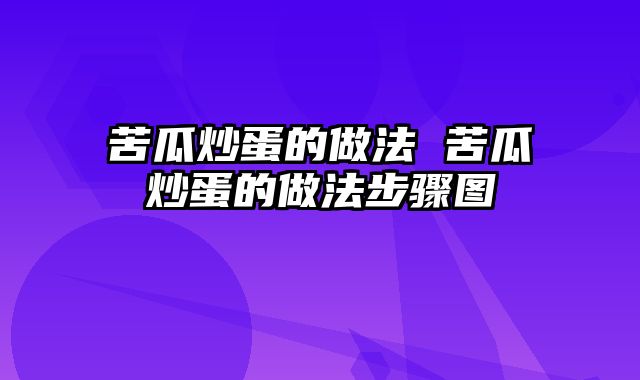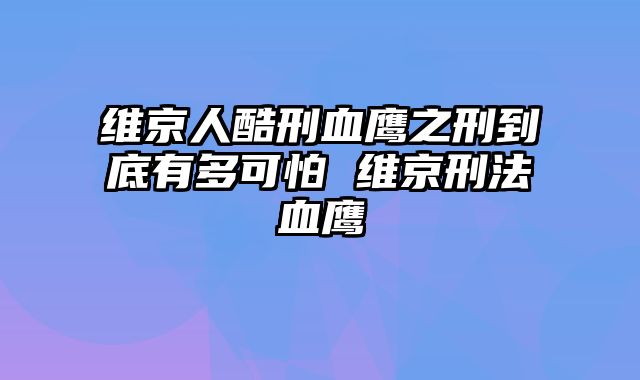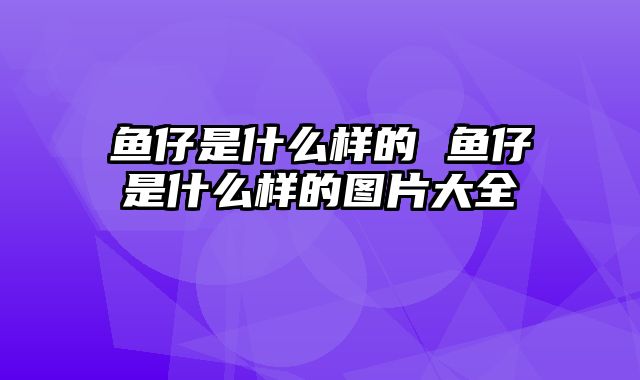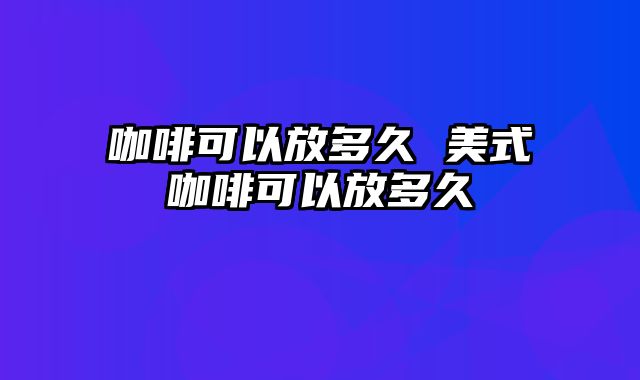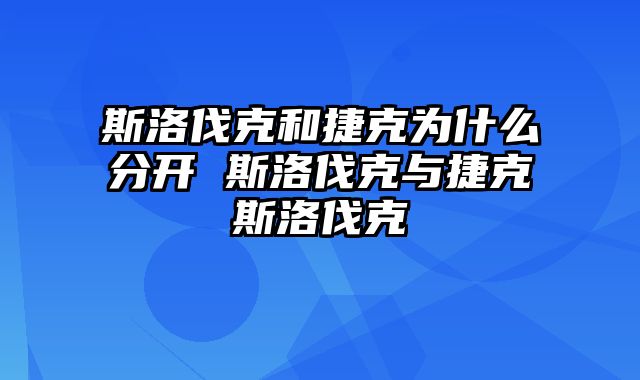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藏作为清朝中央政府直辖的边疆行政区,其主权与领土完整在英帝国殖民扩张浪潮中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自1888年第一次英国侵藏战争爆发,至1904年荣赫鹏率军攻陷拉萨,英军以“通商”“勘界”为名,行军事侵略与政治渗透之实,深刻暴露了晚清国家能力衰微、边疆治理体系崩解与列强“以夷制边”战略的残酷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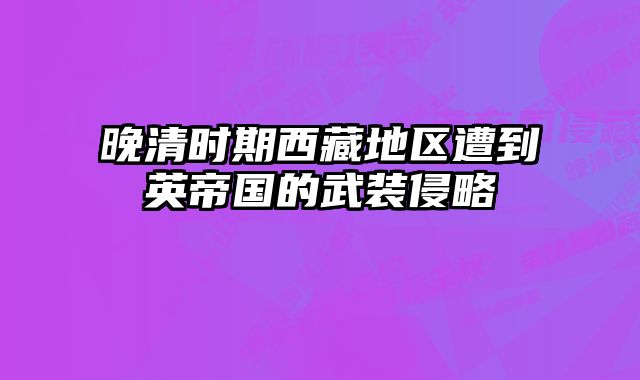
1886年,英印当局以哲孟雄(今锡金)归属问题为借口,要求清廷开放亚东为商埠,并派员入藏“通商”。清廷虽据《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承认哲孟雄归英保护,但明确拒绝英人入藏。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则坚持“藏地不与外人通商”的传统政教原则,于1888年在隆吐山设卡戍守。英军随即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以先进后膛枪与阿姆斯特朗炮击溃藏军火绳枪与土炮武装,隆吐山失守,藏军伤亡逾千,而英方仅数十人负伤。此役并非孤立军事冲突,而是英属印度“西北边疆安全观”向喜马拉雅纵深延伸的战略支点——控制西藏即扼住中国西南咽喉,阻断俄势力南下,同时攫取通往内地的贸易通道。
清廷反应迟滞且矛盾:驻藏大臣文硕主战获藏民拥戴,却被清廷革职查办;继任者升泰转而推行妥协路线,于1893年签订《中英会议藏印续约》,被迫开放亚东为商埠,准许英人在该地免税贸易五年,并默许英人“勘界”特权。此举非但未能换取和平,反被英方视为软弱信号。1903年,英国以“边界纠纷”和“藏方违约”为由,由上校弗朗西斯·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率3000余英印联军携马克沁机枪、山炮及无线电设备再度侵藏。面对藏军以血肉之躯持刀矛、火绳枪在曲美辛古、江孜宗山等地殊死抵抗,英军以绝对技术代差实施精准火力覆盖。江孜宗山保卫战持续三个月,藏军弹尽援绝后集体跳崖殉国,史称“江孜抗英十三勇士”实为数百无名僧俗义士。1904年8月3日,英军兵临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蒙古,噶厦被迫签订《拉萨条约》——规定赔款50万英镑、拆除自印度至江孜沿途所有防御工事、开放噶大克等三处商埠、英可在春丕谷驻军两年。
值得注意的是,《拉萨条约》并未获得清廷正式批准。外务部大臣瞿鸿禨、驻藏大臣有泰等虽消极应对,但清廷最终以“未经朝廷允准”为由拒签,并于1906年与英国重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将《拉萨条约》作为附约纳入,同时首次在国际条约中明文载入“英国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条款。这一看似让步的文本,实为清廷在极度弱势下以法理手段捍卫主权的艰难努力——它首次迫使列强在条约中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为日后民国及新中国处理涉藏外交埋下关键法理伏笔。
更深层看,英帝国侵藏本质是殖民现代性暴力对前现代边疆秩序的碾压。英国不仅输出枪炮,更系统推行测绘、邮政、电报、海关制度,在亚东设立英印邮政局、委任“商务委员”,将西藏逐步纳入英印经济辐射圈。与此同时,清廷于1906年任命张荫棠为“查办藏事大臣”,推行“新政”:废除乌拉差役、整顿吏治、兴办汉藏双语学堂、设立劝业道发展羊毛纺织业。赵尔丰随后在川边实行“改土归流”,强化川藏交通(修筑川藏大道雏形),这些举措虽因清亡而中断,却标志着中央政权首次尝试以现代行政与经济手段重构西藏治理结构。
历史的吊诡在于:英军用枪炮打开的商埠,最终成为西藏接触外部世界的第一扇窗;清廷仓促启动的改革,又为20世纪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边疆整合提供了早期范式。今日回望这段历史,隆吐山的残垣、江孜宗山的弹痕、罗布林卡保存的《拉萨条约》汉译本原件,共同构成一部立体的边疆主权教科书——它警示我们:主权不是抽象概念,而是由驻军、税关、邮驿、学堂与无数无名者以生命守护的日常实践;边疆稳定从不取决于地理距离,而系于中央治理能力、制度韧性与民众认同的深度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