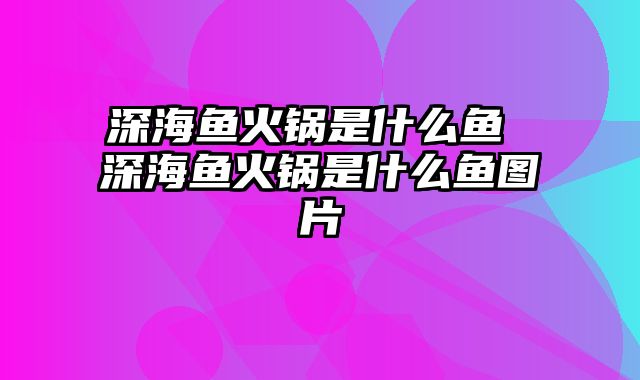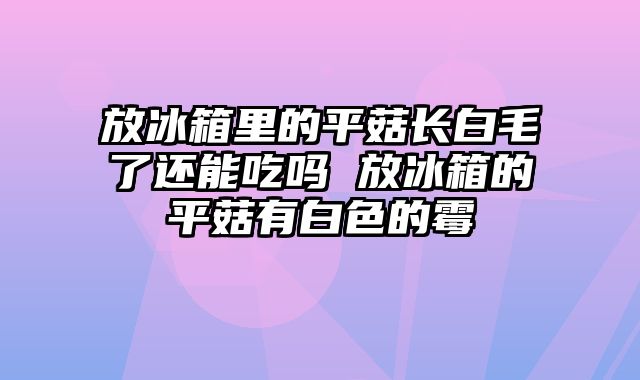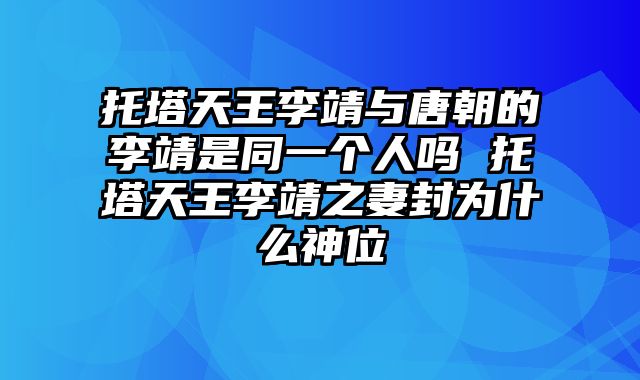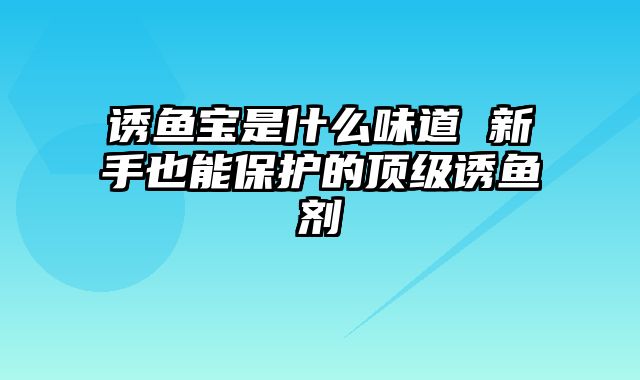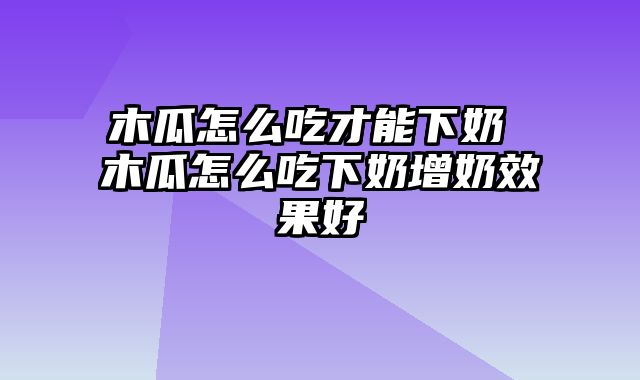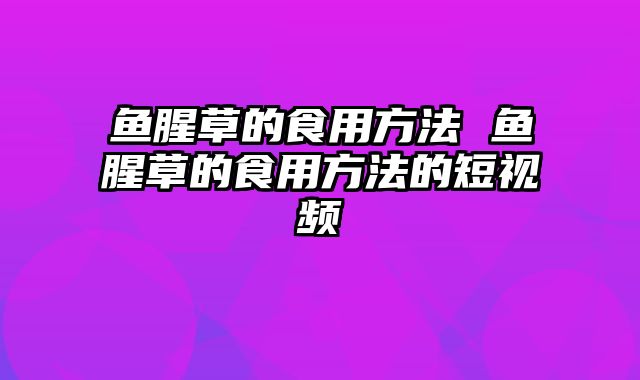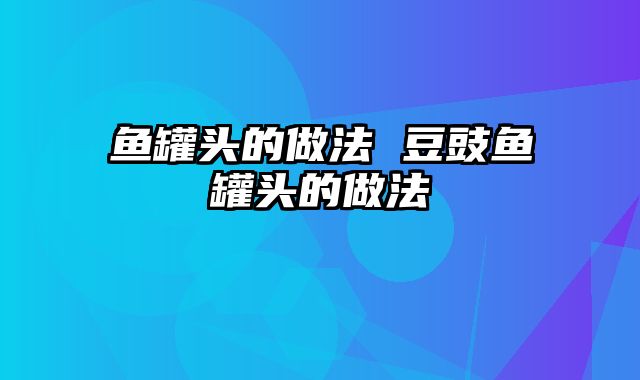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高俅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作为北宋末年的重要官员,他并非通过科举正途入仕,而是凭借擅长蹴鞠(古代足球)而得到宋徽宗的宠信,最终官至太尉,掌握军政大权。这一特殊的晋升路径本身就折射出其性格中的多重特质——机敏圆滑、善于逢迎、深谙权术,同时也暴露出他道德操守的缺失与政治责任感的淡薄。

高俅的性格首先表现为极强的适应能力与生存智慧。据《宋史》及宋代笔记如《挥麈后录》记载,高俅早年出身卑微,曾在苏轼门下做书童,后辗转进入端王府,因蹴鞠技艺出众而受到当时尚为端王的赵佶赏识。这种从文人府邸到皇亲贵胄之间的流转,说明他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的处世哲学。他能准确把握权贵的心理需求,以特长投其所好,从而实现人生跃迁。这种“因势利导”的能力,虽非传统士大夫所推崇的德行,但在现实政治中却极为有效,体现出高俅精于自我包装与人际经营的性格特征。
其次,高俅性格中最为显著的是其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一面。一旦得势,他并未致力于整顿军务、富国强兵,反而利用职权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水浒传》虽为小说,但其中对高俅陷害林冲、迫害忠良的描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对其负面形象的集体记忆。历史上虽无确凿证据证明他直接参与迫害梁山好汉,但他掌管禁军期间,军纪松弛、贪腐成风,导致边防虚弱,实难辞其咎。这反映出他在权力面前丧失原则,以维护个人地位为最高目标,缺乏士大夫应有的家国情怀。
然而,若仅将高俅视为一无是处的奸佞之臣,亦有失公允。部分史料显示,他在任职期间并非全无建树。例如,他对宫廷体育活动的组织与推广有一定贡献,蹴鞠在北宋的鼎盛发展与其推动不无关系。此外,他在艺术审美方面也有一定造诣,深得宋徽宗信任,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皇帝与外朝之间的缓冲角色。但这些建树多服务于皇室享乐,而非国家根本利益,因此其正面影响极为有限。
更深层次看,高俅的性格形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相关。北宋晚期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文官集团内斗不断,整个体制已显颓势。在这样的环境下,像高俅这样善于钻营、不拘小节的人反而更容易上位。他的成功不是个体偶然,而是制度溃败的产物。他之所以能长期居于高位,正是因为宋徽宗沉溺艺术、不理朝政,亟需一个既能娱乐君心又能处理琐务的亲信。高俅恰好填补了这一角色空缺,其性格中的投机性与依附性正是在这种畸形政治生态中被放大和强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高俅并未像蔡京、童贯等人那样被列入“六贼”之列,说明其政治影响力和作恶程度相对有限。他更多是以“宠臣”身份存在,而非真正的政策制定者。这也意味着他的性格中可能缺乏极端的野心与破坏力,而更多表现为一种被动的迎合与自保。他在权力结构中更像是一个“工具性人物”,其行为逻辑始终围绕着如何取悦君主、维持现状展开。
综上所述,高俅的性格是复杂而多面的:他聪明却不用于正道,有能力却不用于国事,有机遇却无担当。他是乱世中崛起的典型宠臣,其圆滑世故、趋利避害的性格特征,既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时代病态的缩影。透过高俅,我们不仅看到一个历史人物的命运轨迹,更窥见北宋末年政治生态的深层危机——当才华不再服务于天下,而沦为取悦权贵的手段时,王朝的崩塌便已悄然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