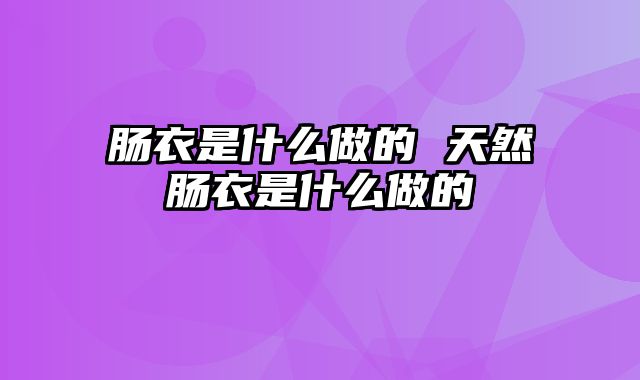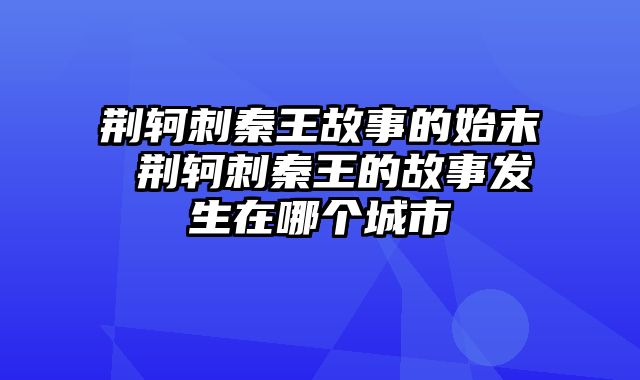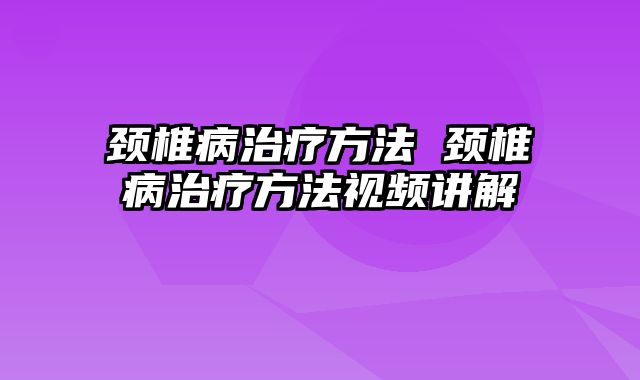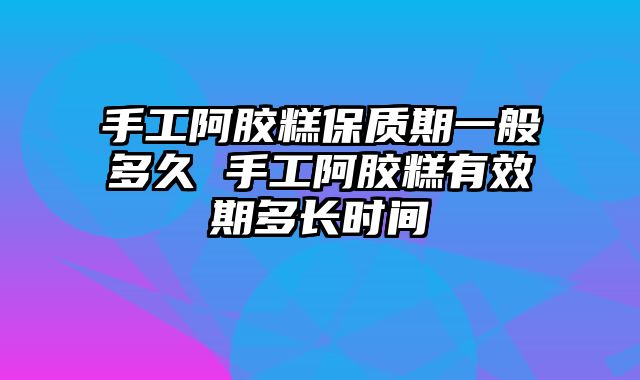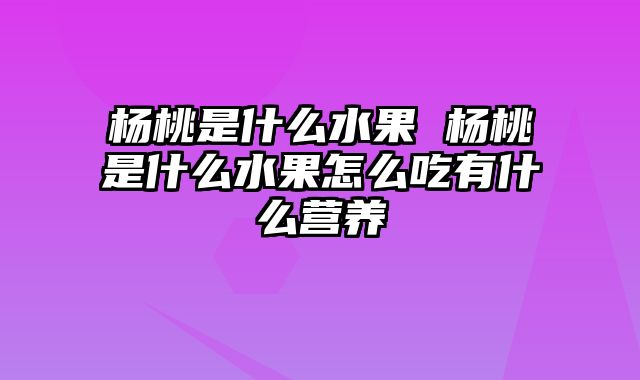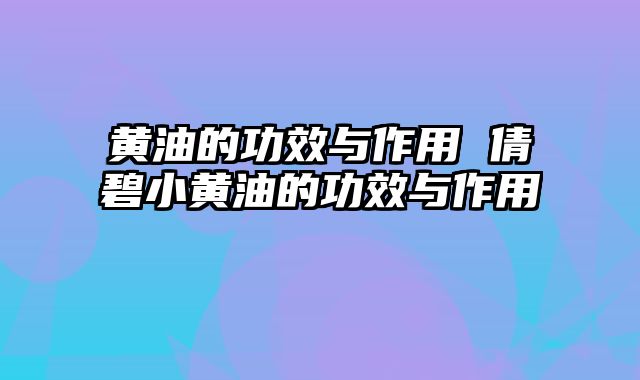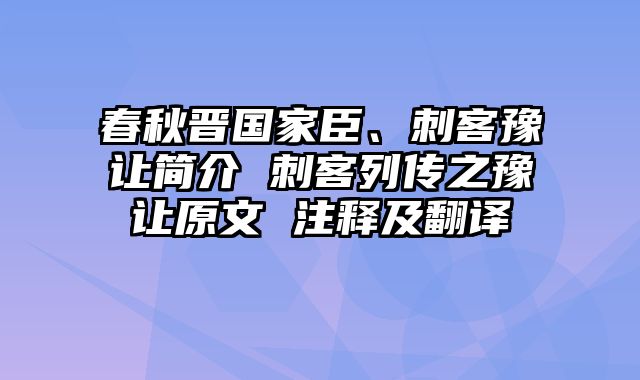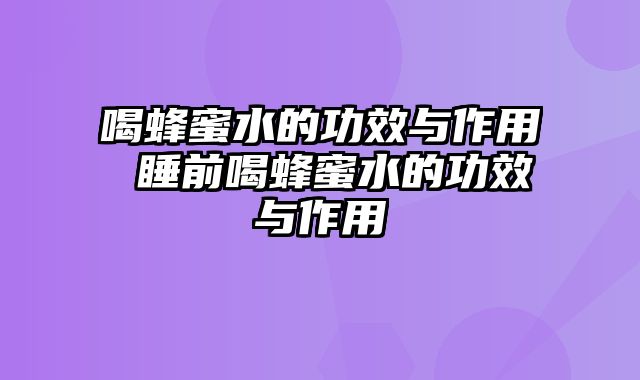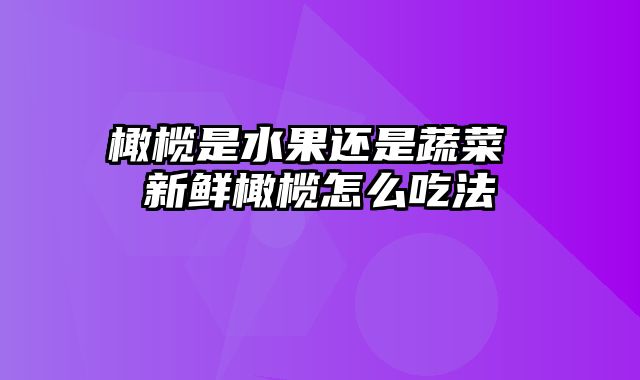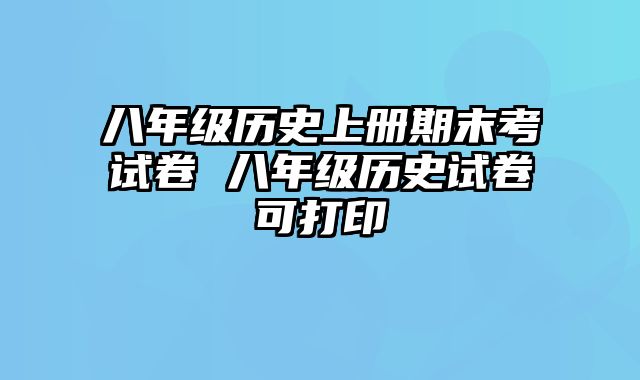继《春秋》之后,编年体在战国至秦汉时期逐步发展完善。左丘明所作的《左传》是对《春秋》的详细注解与补充,不仅丰富了原始记载,还通过叙事手法增强了历史的可读性与完整性。《左传》以详实的史料、生动的描写和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将编年体推向成熟阶段,成为后世史家推崇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竹书纪年》作为战国时期魏国的编年史,也展现了不同于儒家正统视角的历史记录方式,其内容涉及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诸多事件,虽曾一度失传,但清代以来的辑佚工作使其部分内容得以重现,为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进入汉代,司马迁虽以《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但编年体并未因此衰落。相反,在东汉班固所撰《汉书》的影响下,官方修史逐渐重视时间序列的完整性。而真正使编年体再次焕发生机的是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这部历时十九年完成的巨著,涵盖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备的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在编修过程中强调“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旨在为统治者提供治国理政的历史借鉴,因而该书不仅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更体现了强烈的政治实用性。
《资治通鉴》的编纂方法极为严谨,司马光组织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学者分工协作,先编写“长编”,再由其本人删定成书,确保内容真实可靠。此外,他还撰有《通鉴考异》三十卷,专门说明史料取舍依据,开创了史学考据的先河。这种科学严谨的态度,使得《资治通鉴》在后世被视为编年体史书的巅峰之作,并催生了大量续作与仿作,如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进一步拓展了编年体的应用范围。
相较于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的叙述方式,编年体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清晰展现历史发展的纵向脉络,便于读者把握时代变迁的整体趋势。尤其在分析重大历史转折、制度演变或战争进程时,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记录方式更能凸显因果关系与连续性。例如,《资治通鉴》中对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王安石变法等事件的详尽记述,均体现出时间线索在揭示政治动态中的独特作用。
然而,编年体也有其局限性。由于必须严格遵循时间顺序,同一时期不同地域或人物的事件可能被分散记载,导致叙事碎片化,难以形成完整的人物形象或专题论述。为此,后世学者常将编年体与其他体裁结合使用,如采用“纲目体”(即纲为提要,目为详述)来增强条理性,或辅以志、表等形式补充制度与人物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编年体不仅在中国历史悠久,也在东亚文化圈广泛传播。日本的《日本书纪》、朝鲜的《高丽史》以及越南的《大越史记全书》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编年体传统的影响。这表明,以时间为轴心的历史书写模式,具有跨文化的普适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编年体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春秋》发端、《左传》成熟、《资治通鉴》集大成的发展过程,不仅承载了丰富的历史记忆,也塑造了中国人理解历史的基本方式。它强调时间秩序、注重因果关联、追求政治借鉴的功能定位,至今仍对历史研究与公共认知产生深远影响。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新时代背景下,编年体的形式也被应用于现代历史数据库与时间轴工具中,继续发挥其梳理复杂历史进程的独特优势。
编年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编纂的重要体裁之一,以时间为主线,按年、月、日顺序记录历史事件,具有清晰的时间脉络和系统的历史记载特点。这种史书形式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春秋》作为鲁国的官方编年史,被公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相传由孔子修订而成,《春秋》不仅记录了鲁国十二位君主在位期间的重大政治、军事与外交事件,还蕴含了儒家“正名”“尊王攘夷”的政治理念,被誉为“微言大义”的典范。其语言简练,用词严谨,一字寓褒贬,形成了独特的“春秋笔法”,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