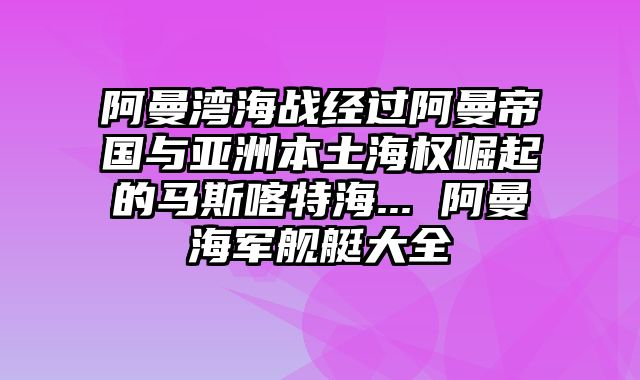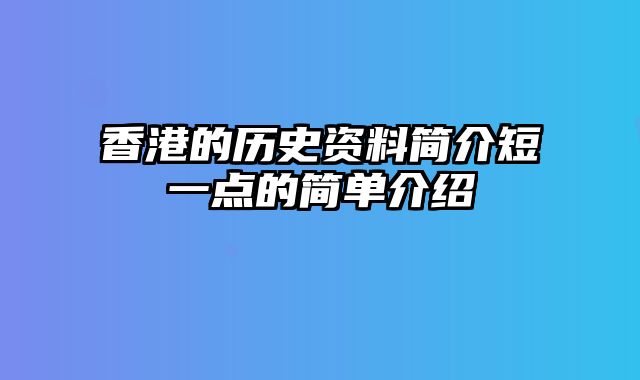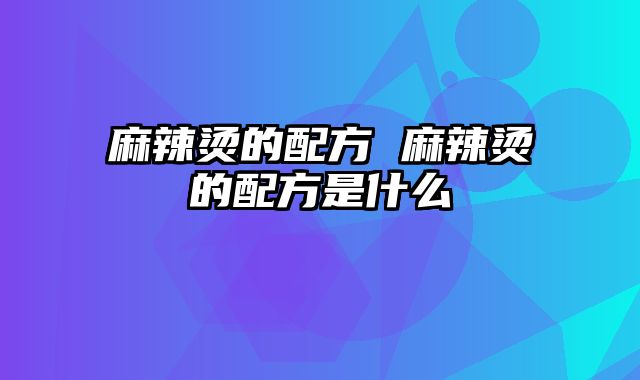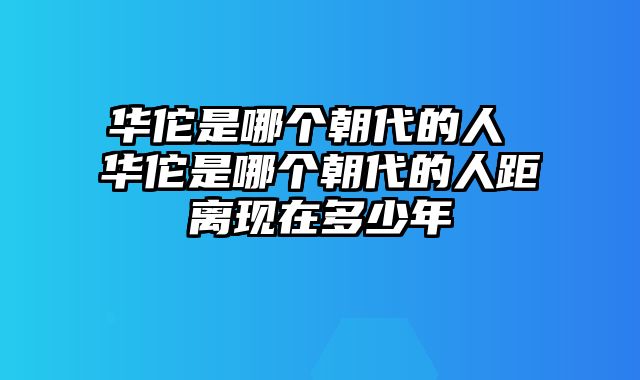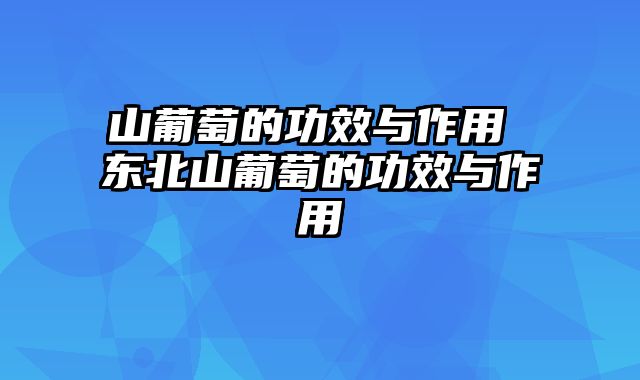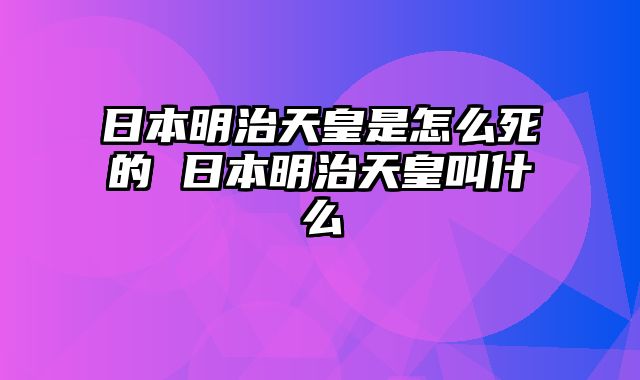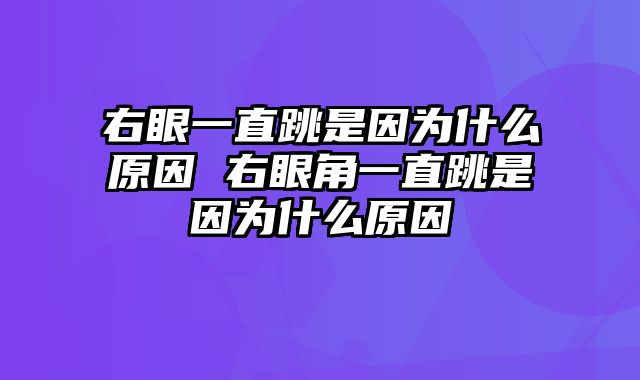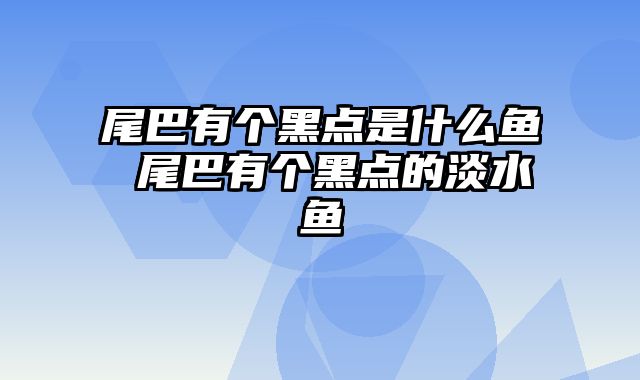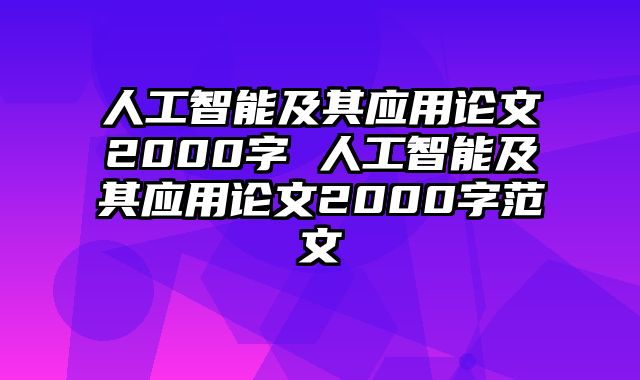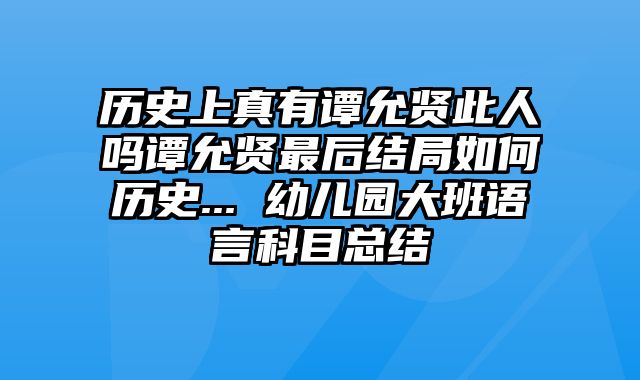古印度宗教的源头可追溯至印度河谷文明(约公元前2600–1900年)。摩亨佐-达罗遗址出土的“瑜伽冥想者”印章、母神陶俑与公牛图腾,暗示着早期冥想实践、生殖崇拜与动物神圣化的雏形。虽其文字尚未破译,但这些意象已悄然嵌入后世印度教仪轨:如湿婆作为“舞者”与“瑜伽之主”的双重形象,或难近母作为创生与毁灭一体的女神原型,均可在此觅得远古回响。雅利安人东迁后带来的吠陀传统,并未取代原有信仰,而是通过“吸收—转化”机制将其纳入新体系:河谷文明的蛇神纳迦被升格为护法神,地方水神融入恒河女神伽格拉的化身叙事,甚至佛陀本人在往世书时代被列为毗湿奴十大化身之一——这种柔性整合能力,正是印度宗教韧性的核心密码。

印度教作为现存最广义的印度宗教主体,实为“千面一体”的实践集合。它没有统一教会、不成文教典,亦无绝对教宗。《薄伽梵歌》强调“诸道归一”:行动之道(羯磨瑜伽)、智慧之道(智瑜伽)、虔信之道(巴克提瑜伽)与禅定之道(王瑜伽)各适其人;《奥义书》则直指“梵我一如”——个体灵魂(阿特曼)与终极实在(梵)本质同一。这种哲学深度与实践弹性,使印度教能持续吸纳新思潮:公元8世纪商羯罗以“不二论”重释吠陀,13世纪罗摩奴阇提出“有限不二论”,16世纪柴坦亚将巴克提推向情感狂喜,19世纪辨喜更以英语向西方阐释“吠檀多普遍主义”,宣称“所有宗教都是通向同一真理的不同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宗教的多元性绝非静态拼贴,而是充满张力的动态对话。佛教虽在印度本土于12世纪后式微,但其“无我”“缘起”思想深刻重塑了印度教的哲学论辩;耆那教严守“不害”(ahimsa)戒律,直接影响甘地非暴力运动的伦理根基;锡克教15世纪诞生于旁遮普,融合伊斯兰苏菲派的一神观与印度教轮回观,以《阿底格兰特》为圣典,强调劳动、祈祷与分享三位一体,成为跨越种姓与性别壁垒的平等共同体。即便穆斯林统治时期,苏菲圣徒常与印度教苦行僧同居一洞,共享鲁布拉诗与卡瓦力歌谣;在喀拉拉邦,印度教寺庙与穆斯林清真寺共享同一片椰林,节庆时互赠甜点与油灯——信仰边界在此不是高墙,而是可穿越的溪流。
当代印度宗教生态依然鲜活而复杂。瓦拉纳西恒河畔,晨光中婆罗门祭司诵《夜柔吠陀》,旁侧佛教僧侣静坐禅修,耆那教徒赤足扫地以防误伤微生,锡克教义工(kar seva)正为所有人分发免费餐食(langar)。这种日常共在,不是文化标本式的展示,而是数千年“容忍即修行”传统的自然延展。当然,政治化宗教冲突亦曾撕裂社会,但民间层面的交织从未中断:泰米尔纳德邦的“阿马尔纳特朝圣”路上,穆斯林摊贩为印度教香客提供冰水;拉贾斯坦邦的庙会集市里,锡克教徒与印度教徒共同抬神轿巡游。人类学家麦金托什指出:“在印度,宗教身份常如纱丽褶皱——层层叠叠,彼此透光,而非铁板一块。”
印度宗教的真正启示,在于它揭示了一种可能:多样性不必导向分裂,差异可以成为理解自身的镜子。当全球面临文明冲突焦虑之时,印度经验提醒我们——信仰的深度,未必取决于排他性的绝对真理,而在于对生命复杂性的敬畏、对他人道路的尊重,以及在永恒追问中保持开放的能力。这并非模糊立场,而是一种更艰难的坚守:在纷繁中认出共相,在差异里触摸同一。
印度宗教并非单一信仰体系,而是由数千年历史层积而成的活态精神网络。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梨俱吠陀》吟唱的自然神祇,到公元前6世纪佛陀在菩提伽耶树下觉悟、大雄创立耆那教、以及稍后兴起的性力派与湿婆派实践,再到中世纪巴克提运动掀起的民间虔信浪潮,印度宗教始终以“多维共存、内在转化”为根本特质。这种独特性,在世界宗教图谱中极为罕见——它不以排他性教义为根基,而以“达摩”(dharma,即宇宙秩序与个体本分)、“业”(karma,行为及其果报)、“轮回”(samsara)与“解脱”(moksha)四大支柱统摄诸说,使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伊斯兰苏菲派乃至地方性纳迦崇拜、村社女神信仰,皆能在同一地理空间与心灵场域中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