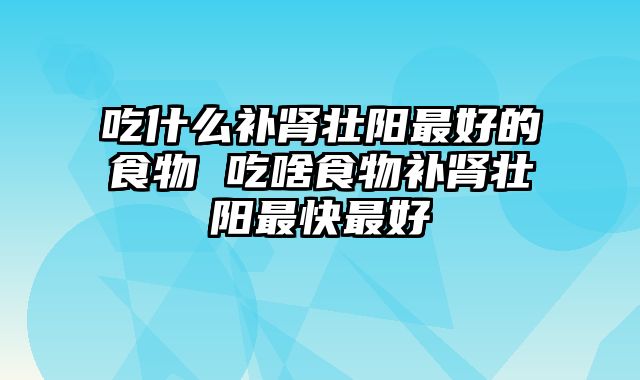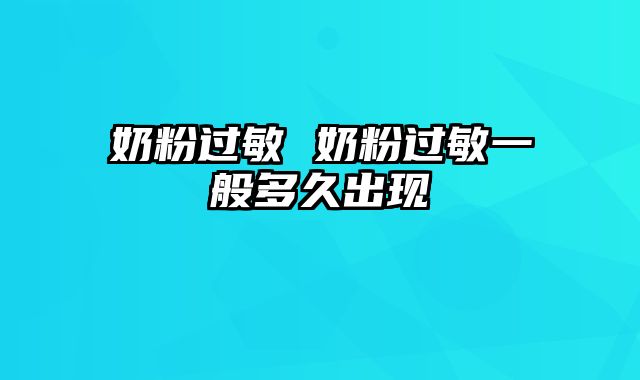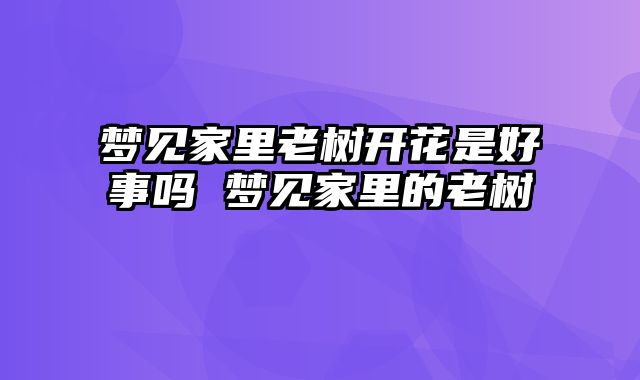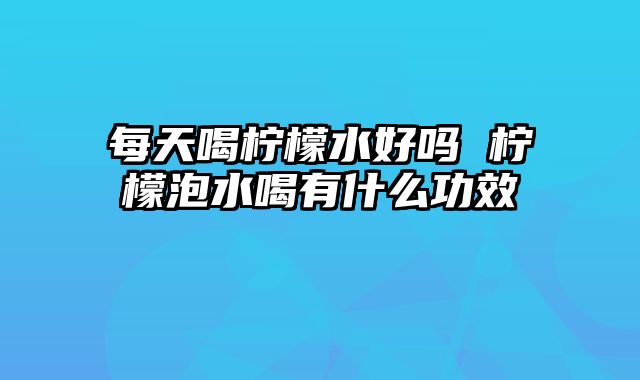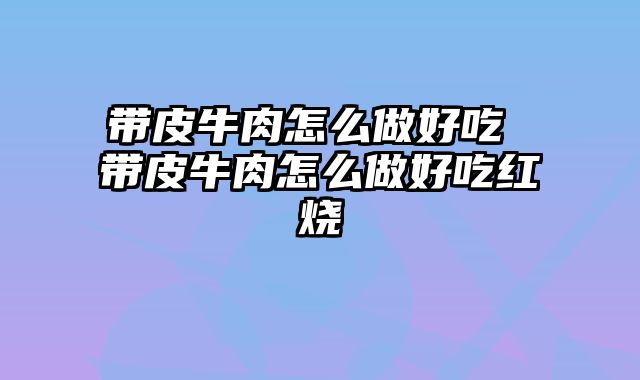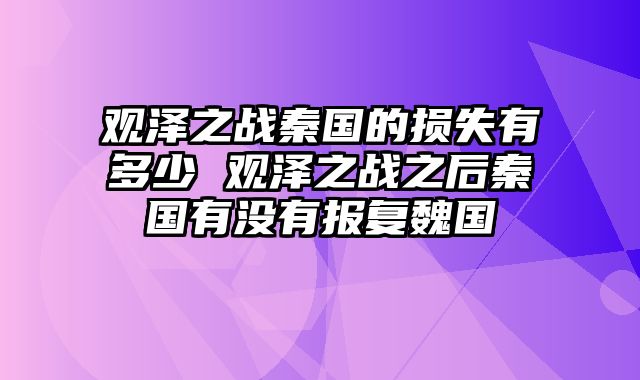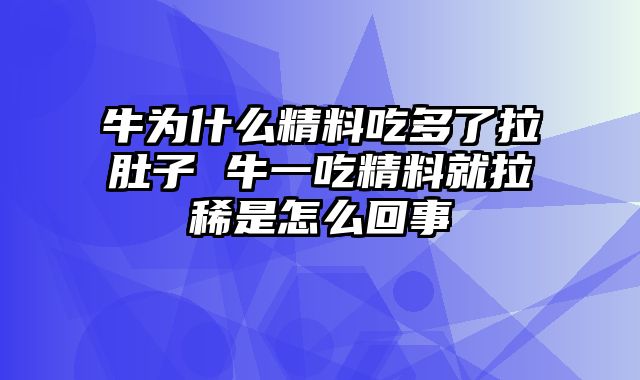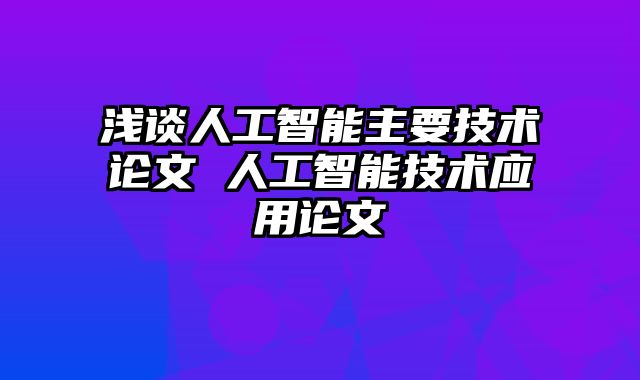三眼铳的物理构造决定了其核心战术定位:非远程精确打击,而是中近距离的集群压制与心理震慑。标准制式三眼铳全长约50–65厘米,铳管外径约2.2–2.8厘米,每管内径约1.1–1.3厘米,可装填约5–8克黑火药及铅子或铁砂。三管呈120度夹角分布,虽共用一个火门,但通过旋转铳身依次点燃各管,实现三次快速连续发射——这一机制虽受限于装填效率与药室余烬风险,却显著优于单发鸟铳的再装填时间(后者需吹膛、装药、压弹、安引信等至少15秒以上)。实战中,士兵常以“三响齐震”制造声势,配合长矛手发起冲锋,形成“火—刺”协同节奏。

就实际杀伤力而言,三眼铳在5–15米内具备极强终止能力。明代兵书《练兵实纪》载:“三眼铳近发,铅子透重甲,铁砂散射如雨,十步之内,人马俱靡。”考古实证亦佐证此说:2013年辽宁兴城明长城遗址出土的一批三眼铳残件,经火药残留检测与弹道模拟复原,证实其初速约240–280米/秒,有效杀伤距离虽仅20米左右,但在10米内铅丸动能可达180–220焦耳,足以击穿1.5毫米厚熟铁甲(相当于明代中级锁子甲或棉甲衬铁片),对无甲目标则可造成贯穿伤或大面积软组织撕裂。若改用霰弹模式(装填铁砂+碎铁片),其10米内覆盖直径达1.8米,命中概率较单发铳提升3倍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三眼铳的“威力”不能脱离明代军事体系孤立评估。它并非替代鸟铳或佛郎机炮的战略级火器,而是填补了火器火力间隙的战术补充。在车营布阵中,三眼铳手常列于战车之后,待敌骑突入车隙时猝然齐射;在夜袭或巷战中,其短小便于挥击的特性更被延伸为钝器使用——铳柄末端常加重铸铁,三管放尽后可抡砸敌首,故民间又称“铳棍”。这种“一器三用”(射击、威慑、格斗)的设计哲学,体现明代军工务实主义的巅峰智慧。
然而,其局限性同样鲜明:射程短、精度差、易炸膛、受潮即失效。《神器谱》直言:“三眼铳利在猝发,不利远准;利在群用,不利单操。”万历年间辽东边军曾尝试将其改良为“五眼铳”,终因重心失衡、药室过热而弃用。至崇祯朝,随着西洋燧发枪与红夷大炮技术传入,三眼铳迅速退居二线,仅在地方团练与民间武装中延续使用,清初《皇朝礼器图式》已将其归入“旧式杂器”,标志其军事生命周期终结。
从技术演进史看,三眼铳是冷热兵器过渡期的典型缩影。它未采用定装弹药,未引入机械击发,却以极致的结构集成与战场适应性,在火药纯度低、工匠技艺参差、后勤保障薄弱的明代边镇环境中,实现了火力密度与作战韧性的最优平衡。其真正威力,不仅在于铅丸破甲的物理能量,更在于它重塑了基层士兵的战斗信心——当三声爆响撕裂战场寂静,那升腾的硝烟与灼热铳管,成为明军直面蒙古铁骑与倭寇锋刃时最可倚仗的“心跳节奏”。
今天,三眼铳早已退出实战序列,但其历史回响仍具启示意义:武器效能从来不只是参数堆砌,更是技术逻辑、制度支撑与人因工程三者咬合的结果。在博物馆玻璃柜中静默陈列的斑驳铜铳,所诉说的不仅是明代火器的工艺高度,更是一个古老帝国在变革浪潮中,以务实姿态锻造生存之力的铿锵回音。
明朝中后期,随着火器技术的加速普及与本土化改造,一种结构独特、操作简捷的轻型火门枪——三眼铳,逐渐成为边军、卫所及家丁部队的重要近战装备。它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连发枪”,而是一种将三根单管铳身呈品字形铸为一体、共用一个药室与点火孔的复合式前装火器。其形制常见于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尤以嘉靖、万历两朝为使用高峰,在戚继光《纪效新书》、赵士桢《神器谱》及《武备志》中均有明确记载与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