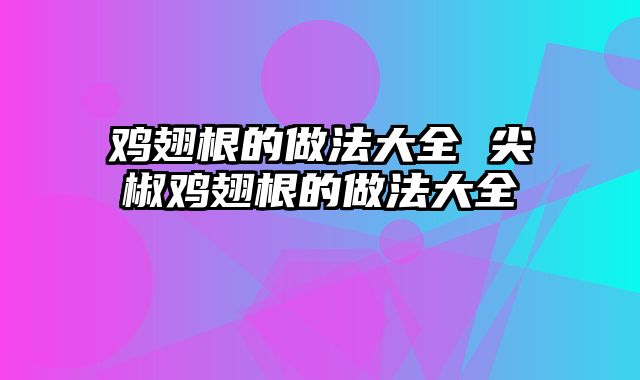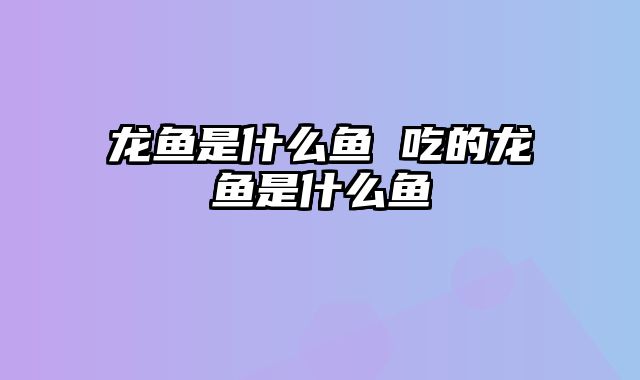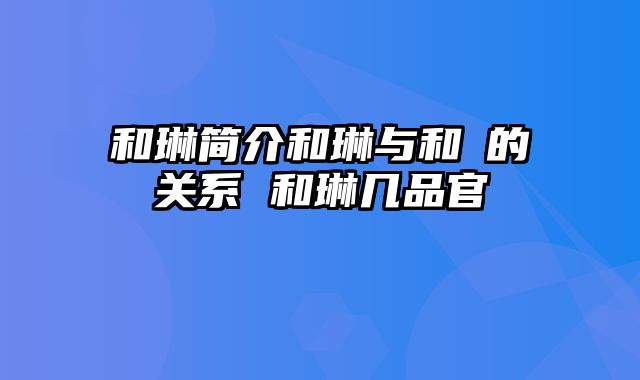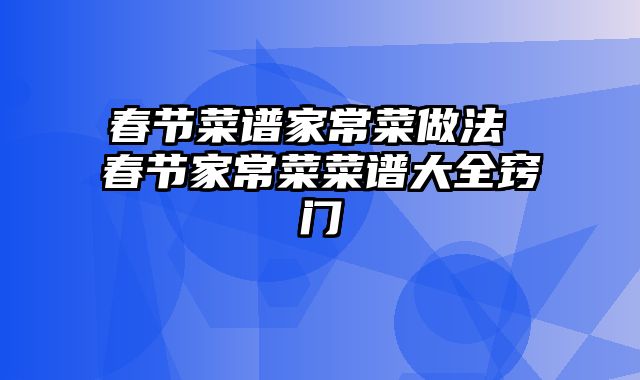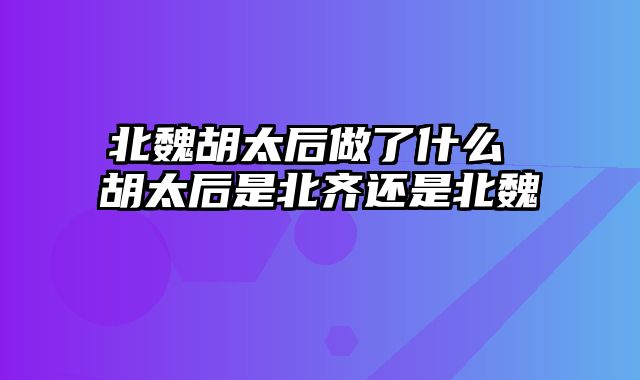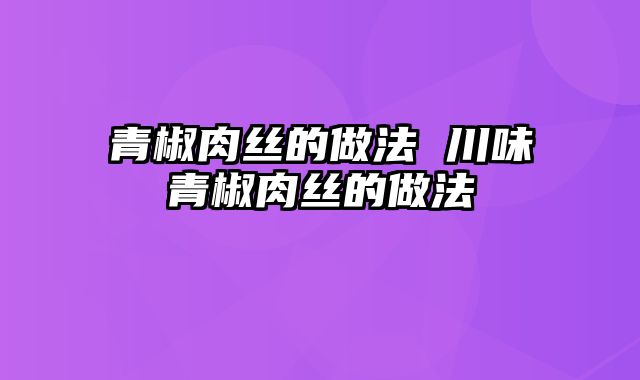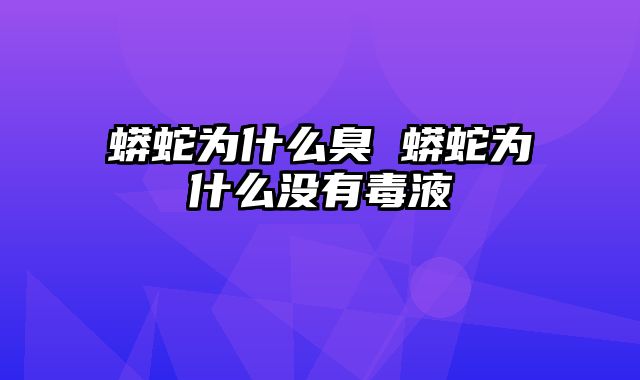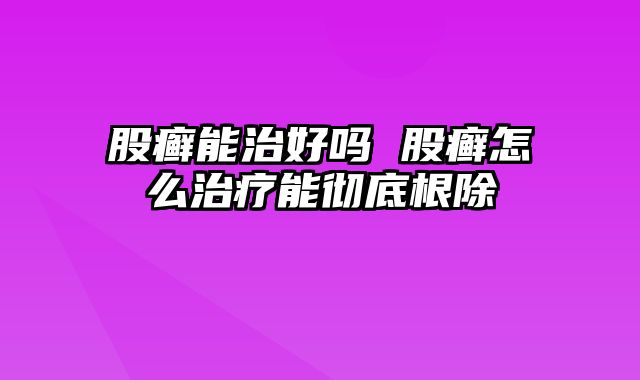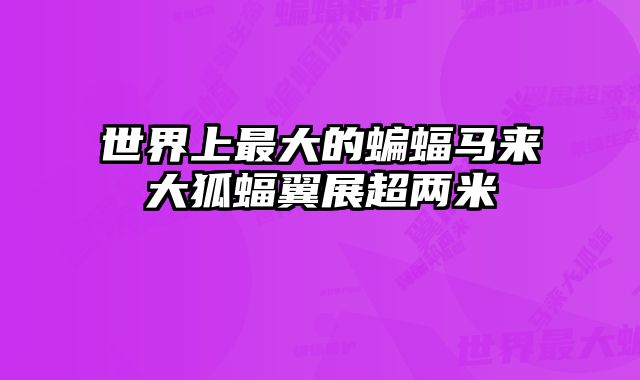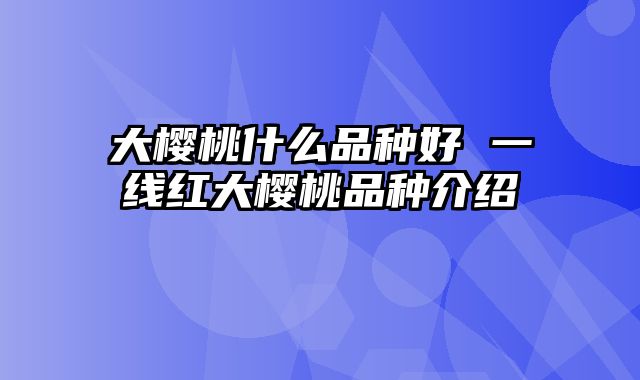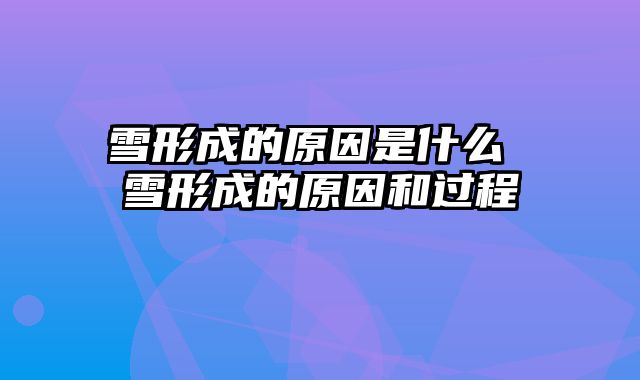《山海经·海内西经》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此处“虚”即“墟”,指高耸通天的神圣台地,而非普通山体。“帝之下都”明确指向天帝在人间的行政中枢,暗示昆仑是宇宙等级制的具象化表达。值得注意的是,昆仑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套于一个精密的神话地理系统:西有弱水、炎火,不可逾越;东有扶桑、汤谷,日出之所;北有幽都,死神所居;南有赤水、黑水,分隔凡圣。这种四极结构,与《淮南子·地形训》所载“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乃有八纮……八纮之外,乃有八极”遥相呼应,构成典型的“同心圆式宇宙模型”,凸显昆仑作为中心原点的绝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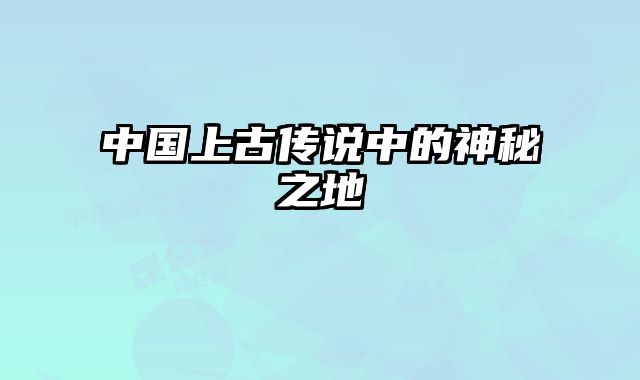
昆仑的神格化还体现于其居民与守护者。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镇守九门,象征对神圣知识的严苛准入;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初为司灾厉疫病之神,后经汉代谶纬与道教改造,渐成掌不死药、主长生的至高女神。《穆天子传》记周穆王西巡至昆仑,与西王母宴饮酬唱,虽具政治隐喻色彩,却印证了昆仑作为王权合法性来源之地的重要功能——君王唯有抵达昆仑、获神谕认可,方能完成“受命于天”的仪式闭环。这一逻辑,可追溯至更早的良渚文化玉琮“神人兽面纹”:中央羽冠神人立于兽背,贯通天地,与昆仑“通天之柱”意象高度同构。
值得注意的是,昆仑意象在历史流变中持续重构。战国至汉初,它被纳入阴阳五行体系,与西方、白色、金德相配,成为秦汉帝国构建“五方帝”宇宙秩序的核心坐标;魏晋以降,随着佛教“须弥山”概念东传,昆仑与须弥山在“山体崇高”“四周环海”“诸天居所”等特征上发生互文融合;至唐宋道教兴盛,昆仑更被坐实为“玄都玉京山”,成为三清道祖显化之境,并衍生出“昆仑派”“昆仑诀”等修炼传统。敦煌遗书P.2526《老子化胡经》甚至称“老子西行入昆仑,化胡为佛”,足见其文化吸附力之强。
现代学者对昆仑地理原型提出多种假说:顾颉刚主张其为“层累造成”的观念产物;丁山考证其名源于塞语“Kunlun”(黑色山峦),或与青藏高原北缘的昆仑山脉有关;饶宗颐则指出,《竹书纪年》载“禹导河自积石,至于龙门,入于沧海”,而积石山古称“昆仑丘”,暗示昆仑可能源于黄河上游先民对高山峡谷的集体记忆。近年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的距今4000年齐家文化玉璧、牙璋,器表刻划螺旋云雷纹与《山海经》所述“昆仑悬圃”云气形态惊人相似;新疆小河墓地出土的木质太阳形祭器与“昆仑日神崇拜”亦存潜在关联。这些发现提示:昆仑信仰或植根于新石器晚期黄河上游至西域走廊的跨区域祭祀网络。
昆仑之“神秘”,正在于其拒绝被单一定义。它既非纯粹虚构,亦非可勘测的坐标;它既是史前萨满登天之梯,也是秦汉方士求仙之途;既是儒家“敬天法祖”的空间投射,也是道教“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修炼场域。当今天我们在敦煌壁画中看见飞天绕昆仑山翩跹,在故宫太和殿丹陛石雕上辨认出“海水江崖”与“昆仑云气”的纹样,在《周易》“艮为山”卦辞中读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我们触摸的,正是那个以昆仑为轴心旋转了四千年的中华精神宇宙——它不提供答案,却始终为文明留存一扇通往崇高、秩序与永恒的未关闭之门。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上古文献与口传记忆中,“昆仑”并非仅是一座地理山岳,而是一个承载宇宙观、神权秩序与文明起源的复合性神圣空间。从《山海经》《淮南子》《穆天子传》到《楚辞》《庄子》,昆仑屡被赋予“帝之下都”“悬圃”“增城”“弱水环绕”“炎火之山”等超验意象,其形象随时代演进而层累叠加,成为理解华夏早期精神世界的关键密码。考古学虽尚未确认其确切地理位置,但昆仑概念本身,早已超越实证地理,升华为一种文化原型——它既是天地轴心(axis mundi),也是人神交通的阶梯,更是道德、知识与永生的终极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