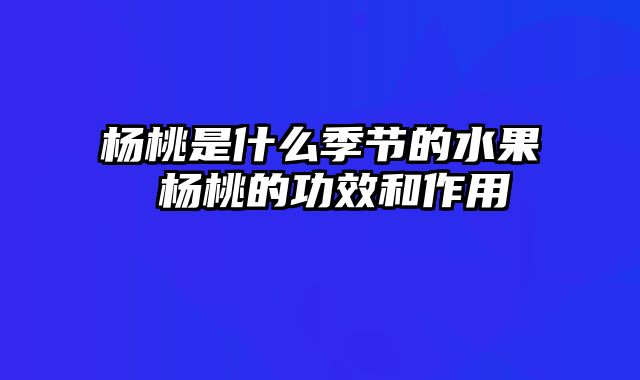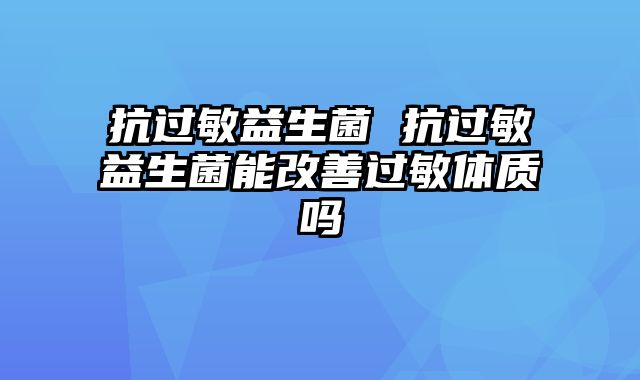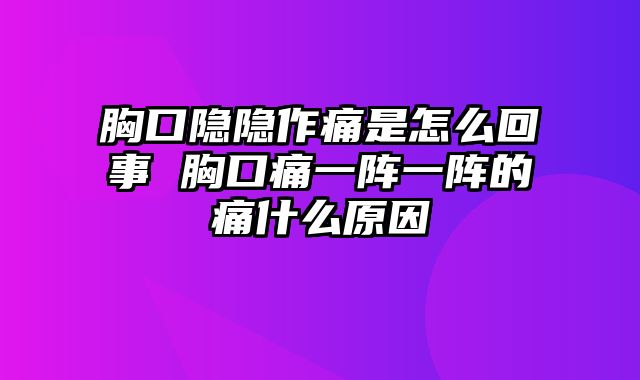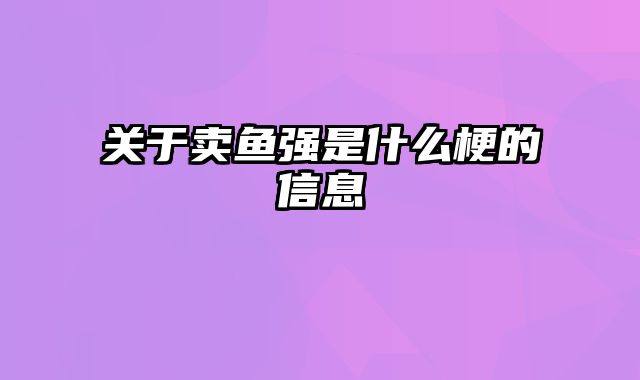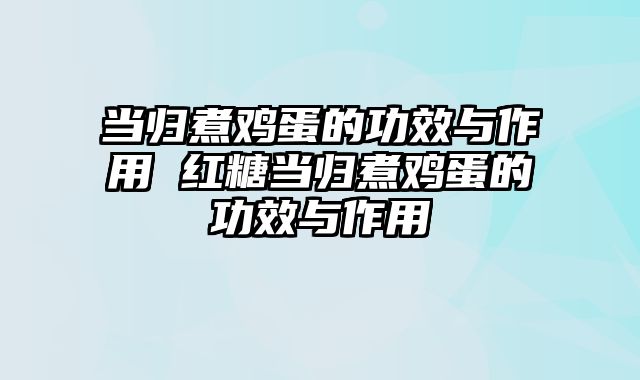唐朝(618—907年)是中国古代服饰发展史上最具创新性、包容性与艺术表现力的高峰时期。其服饰体系既承袭周汉礼制遗绪,又大胆吸纳西域、中亚、南亚乃至波斯、粟特等域外文化元素,在形制、色彩、纹样、材质与穿着观念上均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总体而言,唐朝服饰以“华美繁盛、开放兼容、等级分明而动态演进”为三大核心特点,深刻映射出盛唐社会的自信气度、经济繁荣与文化自觉。

首先,形制上突破前代拘谨,强调人体线条与动态美感。初唐沿袭隋制,男女皆尚窄袖高腰襦裙,但至盛唐,女性服饰发生革命性变化:齐胸襦裙成为主流,裙腰高束至腋下甚至胸部,配以轻薄透纱的披帛,凸显修长身姿;上襦短小精巧,常缀绣金线或织锦边饰;衫、袄、帔、裙组合灵活,形成“三叠式”层叠美学。男子则流行圆领袍衫(即“缺胯袍”),便于骑射与日常活动,官员依品级佩鱼袋、系革带,武官常着甲胄式样改良的“明光铠”便服化变体。值得注意的是,胡服在唐前期极为盛行——翻领、窄袖、条纹裤、蹀躞带、帷帽乃至乌羊毛帽(“浑脱帽”)均源自突厥、回鹘等游牧民族,连唐玄宗本人亦曾“着胡服击鼓”,足见其社会接受度之高。
其次,色彩运用空前大胆且具制度性。唐代实行严格的“品色服”制度: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深红),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庶人则服黄、白二色(后因玄宗尊崇老子,禁庶人穿黄,改许穿皂或褐色)。然而制度并未抑制民间对色彩的热忱。敦煌莫高窟第217、103窟壁画及西安韦氏墓、永泰公主墓出土陶俑显示,贵族女性裙装常见绛红、石榴红、天青、月白、秋香、银灰等十余种色阶,染料来自苏木、红花、蓝靛、栀子、槐米等天然植物,并采用绞缬(扎染)、蜡缬(蜡染)、夹缬(雕版印染)三大工艺,尤以夹缬技术登峰造极——日本正仓院藏唐代“鹿草木夹缬屏风”即为实证,其纹样清晰、色彩饱和、套色精准,代表当时世界印染最高水平。
第三,纹样设计高度程式化又富于象征意涵。唐代服饰纹样分动物、植物、几何、文字四大类。祥禽瑞兽如鸾凤、麒麟、狮子、孔雀多用于皇室与高级命妇礼服;宝相花、团窠牡丹、忍冬纹、葡萄藤蔓则广泛见于织锦与刺绣,其中宝相花乃佛教艺术与中国传统云气纹融合的产物,结构对称、层叠繁复,象征圆满庄严;联珠纹源自萨珊波斯,经丝路传入后本土化为“联珠团窠”,内嵌对鹿、对鸭、狩猎图等主题,体现跨文明对话。值得注意的是,盛唐以后,写实风格花卉纹(如吴道子“吴家样”影响下的折枝花)渐兴,预示晚唐至五代装饰美学的转向。
第四,材质工艺臻于极致,丝绸生产体系冠绝全球。唐代设少府监织染署,统管全国织造,长安、洛阳、定州、益州(成都)、越州(绍兴)为五大丝织中心。其中蜀锦以“冰纨、雾縠、云布”闻名,越州越罗轻如蝉翼,定州绫“薄如蝉纱,丽如晨霞”。考古发现证实,唐代已熟练运用纬锦、重锦、织金、妆花等复杂技法。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其壶身浮雕纹样即模仿当时流行的“舞马纹锦”,侧面印证了服饰纹样与金银器、壁画、石刻的图像互文关系。
最后,穿着观念呈现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个体表达意识。史载“士女皆竞衣胡服”“宫人皆衣袒胸露臂之裙”,白居易《时世妆》讥讽元和年间“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反映民间妆容服饰随风尚快速更迭;而《唐六典》明文规定“妇人裙不过五幅”,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实物却见七幅、八幅大裙,说明礼法约束在实际生活中弹性极大。尤为关键的是,女性可自由参与社交、骑马出游、打马球、观乐舞,其服饰功能随之拓展——高腰裙便于跨鞍,窄袖利于挥杆,帷帽与幂篱则兼顾遮蔽与视野,体现实用主义与审美需求的高度统一。
综上,唐朝服饰绝非静态标本,而是一个流动的文化场域:它既是国家礼制的物质载体,也是丝路贸易的视觉账簿,更是社会心态变迁的晴雨表。从贞观之治的端肃到开元盛世的绚烂,再到安史之乱后的含蓄内敛,服饰风格的每一次微调,都暗合着政治格局、经济结构与思想潮流的深层变动。今日回望唐装,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绫罗锦绣,更是一个古老文明以衣冠为笔、以身体为纸,写就的恢弘文化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