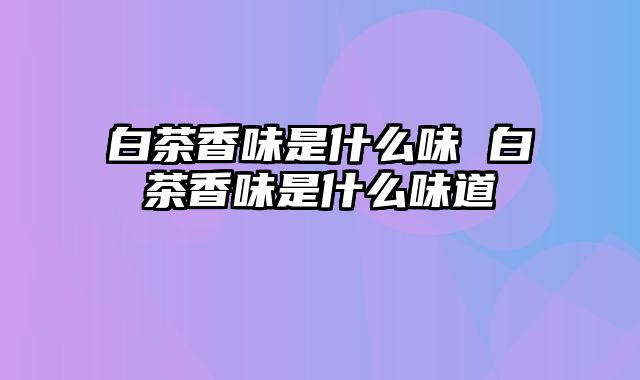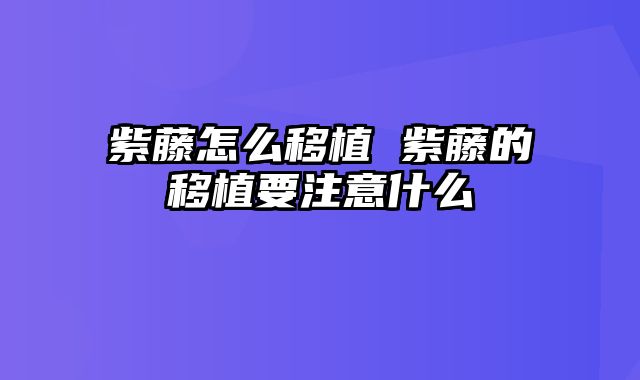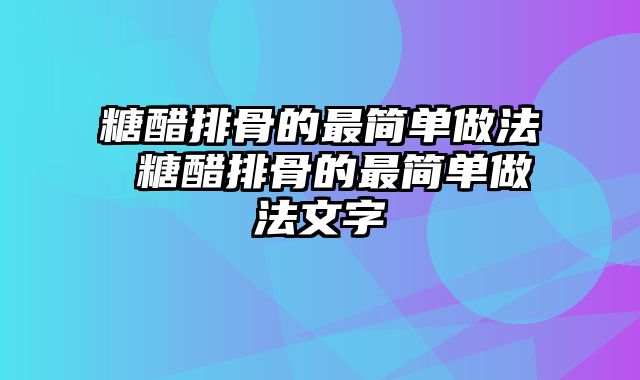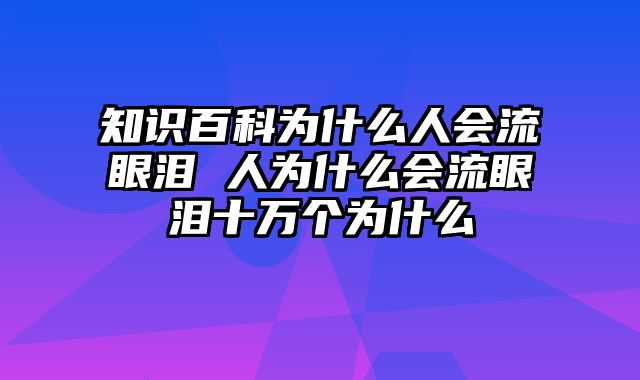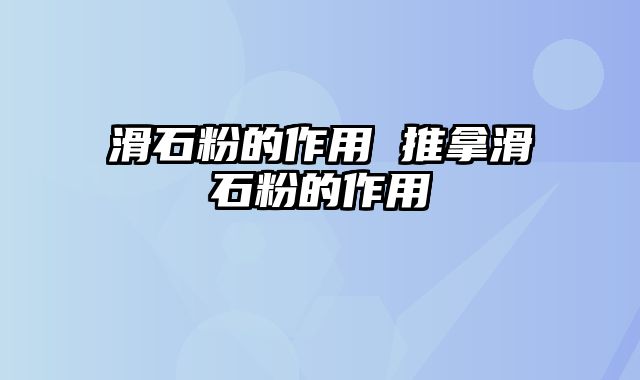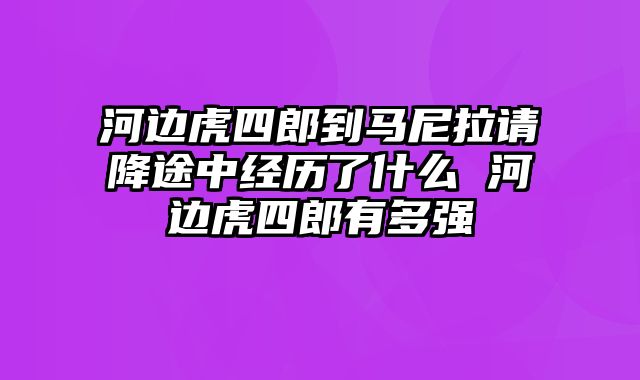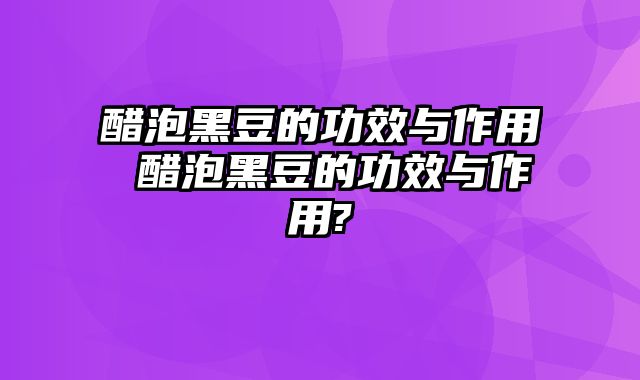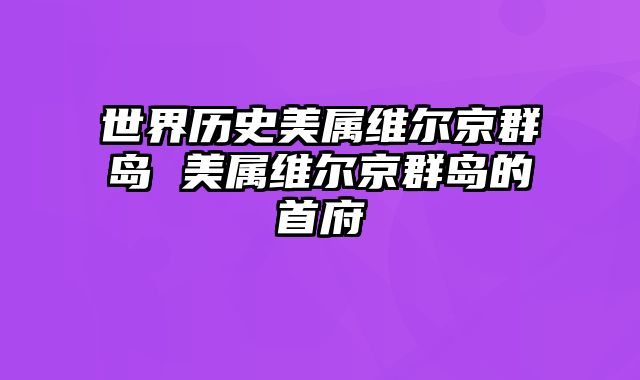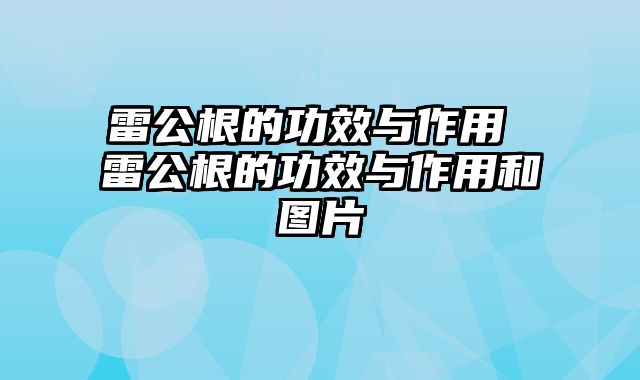1851年金田起义后,杨秀清被封为左辅正军师、东王,节制诸王,“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确立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实际统帅地位。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他总揽军政大权:主持天京筑城与粮运体系重建,设立典官制度分理百务;创设“圣库”制度实现战时资源集中调配;亲撰《天情道理书》系统阐释“天父—天兄—天王”神权谱系,将自身“代天父言”的地位嵌入意识形态核心。军事上,他摒弃流寇式作战,提出“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战略,指挥西征(1853–1856)夺取安庆、九江、武昌,控制长江中游;北伐虽最终失败,但牵制清廷大量兵力,为天京巩固赢得关键时间窗口。史载其“日理万机,批答章奏,不假手于人”,连洪秀全诏旨亦需经其审阅方能颁行。

然而,杨秀清的集权亦埋下致命隐患。他以“天父下凡”屡次斥责洪秀全,甚至逼其跪听训诫;杖责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重臣成常态;更在1856年天京事变前,当众逼迫洪秀全加封自己为“万岁”,逾越君臣名分底线。这一举动绝非一时骄狂,而是其权力逻辑的必然延伸——当“代天父言”成为唯一合法性的来源,而洪秀全的“天王”身份又未完成彻底神格化时,杨秀清的“天父代言人”身份便天然具备更高的神性位阶。清方档案《贼情汇纂》称其“性狡黠,善驾驭,威福自擅”,晚清学者李滨亦评:“秀清以炭徒而操生杀予夺之权,其势不得不张。”
1856年9月,韦昌辉奉洪秀全密诏突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属、部属两万余人被屠戮殆尽,史称“天京事变”。此事标志着太平天国由盛转衰:军事上西征成果部分丧失,长江防线动摇;政治上神权体系崩塌,“天父下凡”沦为笑柄,信仰凝聚力瓦解;组织上洪秀全转向猜忌宗族,重用蒙得恩、洪仁发等庸碌亲信,中枢决策能力断崖式下滑。值得注意的是,杨秀清死后,洪秀全虽下诏追贬其为“乱臣贼子”,却始终未废除东王建制,更在后期《钦定旧遗诏圣书》中悄然恢复其早期功绩记载——这种矛盾态度,折射出历史对其复杂性的无法回避:他既是破坏传统秩序的造反者,又是构建新秩序最有力的设计师;既是践踏儒家纲常的“妖魔”,又是比清廷更高效推行土地均平(《天朝田亩制度》虽未实操,但其理念由杨主导阐释)、妇女解放(女营制度、女官设置)的实践者。
当代史学界对杨秀清的评价日趋多元。简又文指出其“具近代革命家之魄力与手腕”;茅家琦强调其“在农民政权制度建设上的开创性”;而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则提醒:“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而应看到他在19世纪中国基层社会裂变中所展现的惊人适应力与建构力。”杨秀清的悲剧,本质是前现代革命中神权政治与世俗权力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困境:当神圣话语成为唯一合法性来源,任何试图将之制度化的努力,终将反噬其自身。他的名字,早已超越个体生命,成为观察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理想、权力与暴力纠缠关系的一把关键钥匙。
杨秀清(约1823–1856),广西桂平紫荆山区烧炭工出身,无科举功名,不通经史,却以非凡的政治直觉、军事组织力与宗教权术,成为太平天国运动实际奠基者与中期最高实权人物。他并非洪秀全最早的拜上帝会成员,却在1848年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远赴广东营救的权力真空期,借“天父下凡”附体仪式骤然崛起——宣称上帝圣灵附己之身,代天父传言训诫会众。这一创举看似迷信,实为极具现实政治智慧的制度创新:它绕过洪秀全尚未神化的人格权威,直接构建起一套可即时裁决、不容置疑的神圣仲裁机制。杨秀清借此迅速整肃内部、整合紫荆山各股会众,并主导制定《太平条规》《十款天条》等早期纲领,将松散的民间教门转化为具有严密等级、统一号令和战时动员能力的准政权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