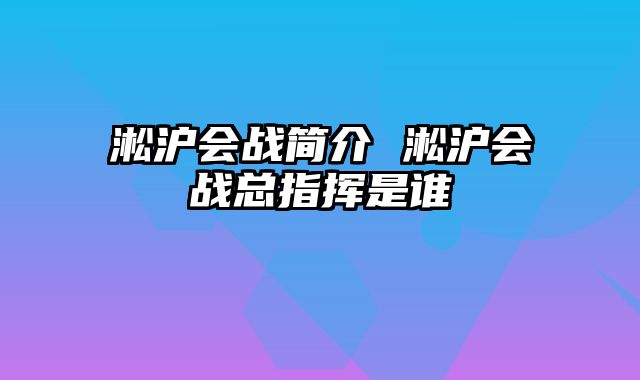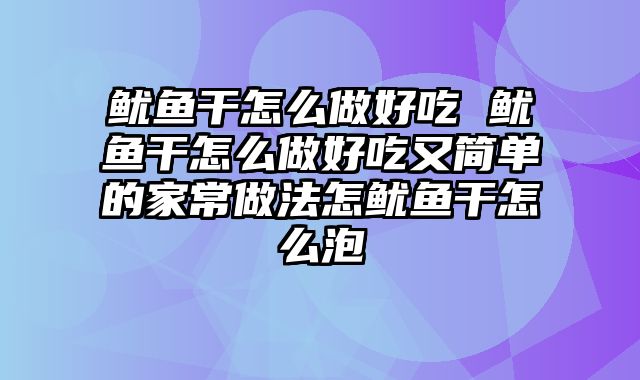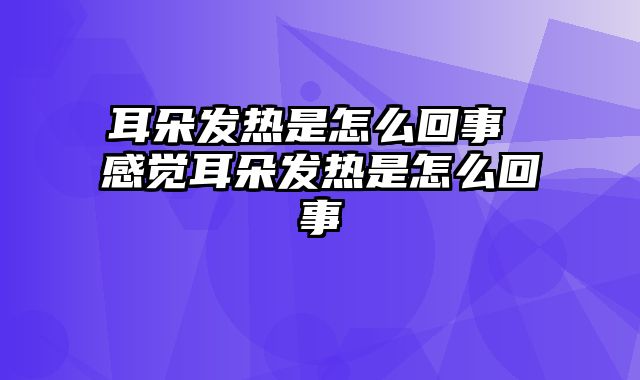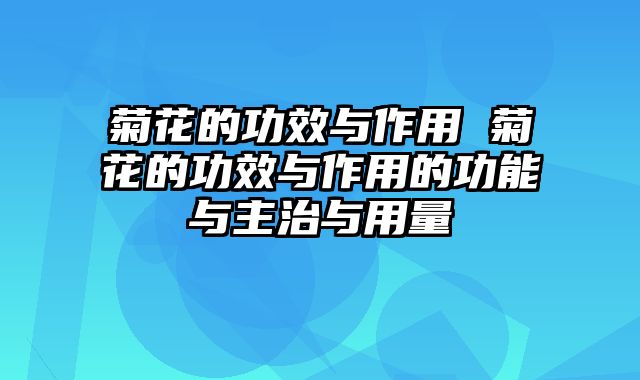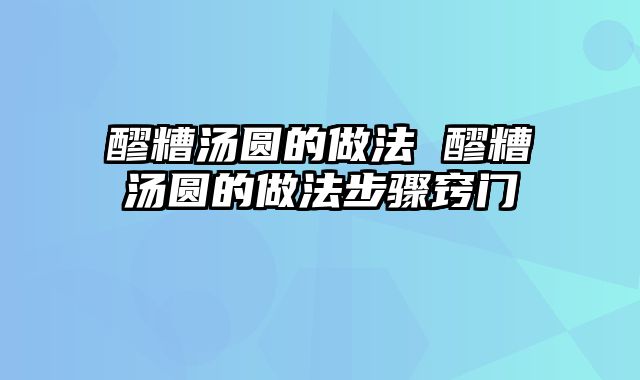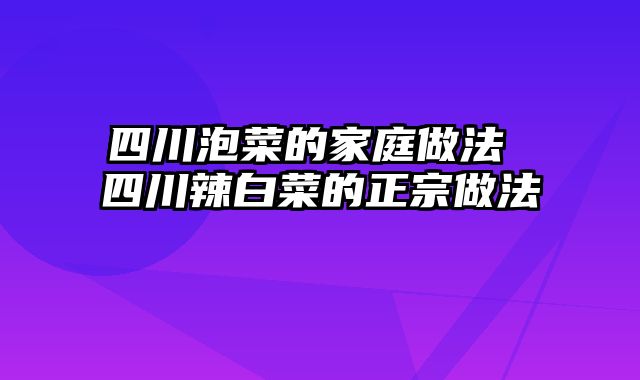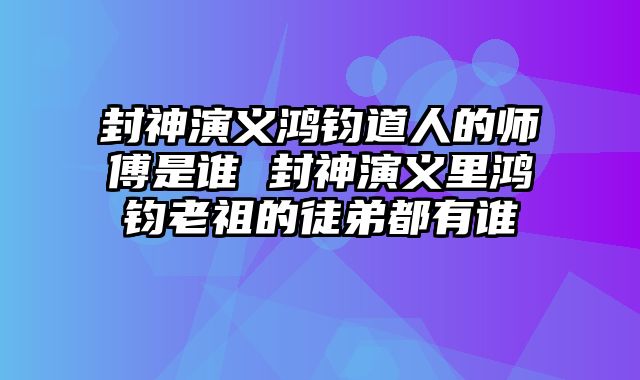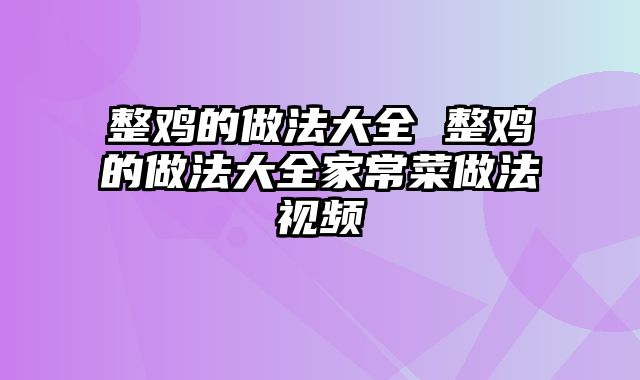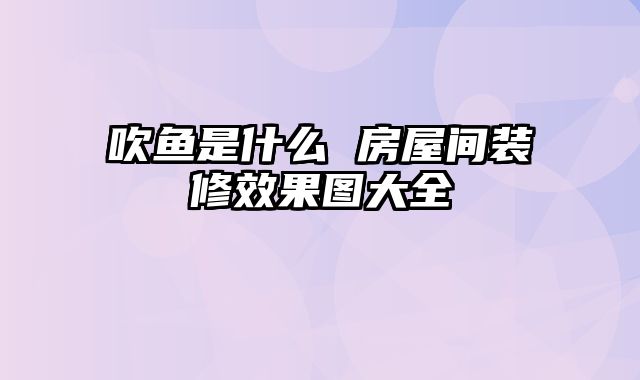耶利哥(今巴勒斯坦西岸杰里科)地处约旦河谷北端,海拔低于海平面约25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有人定居城市之一,亦被公认为人类最古老持续居住地——考古证实其定居史可溯至公元前10000年左右的纳图夫文化晚期。该城在青铜时代中期(约公元前2000–1550年)已筑有坚固泥砖城墙,墙体厚达1.8米,基座嵌入基岩,外侧设斜坡式护墙(glacis),兼具防御与防洪功能。英国考古学家凯瑟琳·凯尼恩(Kathleen Kenyon)于1952–1958年主持的系统性发掘,彻底改写了学界对耶利哥古城年代序列的认知。她通过地层学与陶器类型学分析指出:所谓“约书亚攻陷的耶利哥”,实为青铜时代中期晚期(约公元前1600年)的一座繁荣城市,而到青铜时代末期(约公元前1200年,传统上对应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进入迦南的时间),该城早已荒废逾百年——遗址上层未见任何铁器时代初期(即公元前12世纪)的连续居住层,亦无大规模毁弃灰烬层或武器遗存。换言之,当以色列部落可能进入迦南时,耶利哥并非一座“坚城”,而是一片无人驻守的废墟。

这一结论虽遭部分福音派学者质疑,但后续放射性碳测年(AMS)对凯尼恩所采样本的复核结果高度支持其断代:关键城墙倒塌层的炭样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6世纪中叶,误差范围±30年;而城址在公元前1250年后长达三个世纪内几乎无常住人口痕迹。值得注意的是,青铜时代末期整个东地中海世界正经历剧烈震荡——赫梯帝国崩溃、迈锡尼文明衰落、海上民族大迁徙冲击埃及与黎凡特沿岸,迦南诸城邦普遍陷入政治真空与社会解体。耶利哥的废弃恰是这一宏观危机的微观缩影,而非某次特定战役所致。
那么,《约书亚记》为何将一场早已湮灭的古城毁灭,重构为以色列征服叙事的奠基性胜利?现代历史批判学普遍认为,该文本成形于公元前7–6世纪的犹大王国晚期,甚至可能晚至巴比伦之囚后(公元前6世纪末)。此时的编修者面临严峻的族群认同危机:北国以色列已亡于亚述(公元前722年),南国犹大岌岌可危。重述“约书亚征服”的故事,实为构建“应许之地”的神圣合法性,强调上帝履约、选民得胜的神学逻辑,从而凝聚流散群体、强化土地主张。耶利哥作为迦南最古老之城,其“倒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旧秩序的终结与新圣约的开启。考古上不存在的“第七日呼喊塌墙”,在文本中成为信仰行动力的终极隐喻。
当然,考古并非全然否定所有历史内核。近年对耶利哥周边区域的调查发现,公元前12世纪确有小型农牧聚落渐次兴起,其陶器风格与后来的以色列高地文化存在技术延续性;同时,埃及阿玛尔纳文书(公元前14世纪)提及迦南地区出现名为“哈比鲁”(Habiru)的流动人群,常被视作以色列先祖的社会原型之一——他们非国家军队,而是依附于城邦边缘的武装部族,擅长利用权力真空占据废弃要塞。耶利哥废墟或许曾被此类群体短期占据或仪式性“收复”,后被记忆升华为决定性战役。
此外,耶利哥之战的传播史本身即是一部跨文明接受史。早期犹太拉比文献(如《米德拉什》)强调城墙倒塌乃因居民亵渎安息日;基督教教父奥利金将其解为基督战胜死亡的预表;伊斯兰传统虽未直接记载此役,但《古兰经》中“萨利赫族人之墙崩”等叙事共享相似的道德惩戒母题。直至今日,耶利哥遗址仍矗立着凯尼恩标记的“倒塌城墙”残段,吸引数万访客每年前来触摸那布满裂痕的泥砖——人们触摸的不仅是四千年前的夯土,更是历史、信仰与记忆在时间褶皱中反复叠压的复杂质地。
综上,耶利哥之战的真实面貌并非非此即彼的“纯神话”或“纯史实”,而是一种典型的“记忆考古学”对象:它根植于青铜时代真实的地理枢纽与城市兴废,经由铁器时代晚期的政治需要与神学编纂被重塑,又在近现代科学方法介入后持续激发新的阐释张力。理解这场战役,最终指向的不是验证某句经文的字面真确,而是读懂古代人群如何以故事锻造身份,以废墟铭刻信念,以传说维系一个民族穿越断层线的历史韧性。
耶利哥之战,作为《希伯来圣经·约书亚记》中开篇即载的标志性军事事件,长久以来既是信仰叙事的核心桥段,也是古代近东史与考古学激烈交锋的焦点战场。据《约书亚记》第六章记载,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后,在神谕指引下,连续七日绕行耶利哥城——首日一次,第六日六次,第七日七次,祭司吹角、百姓呼喊,城墙“就塌陷了”,随后全城被焚毁,“连人带牲畜,并一切所有的”尽行灭绝。这一充满超自然色彩的叙述,自中世纪以降便引发神学诠释热潮;而自19世纪末科学考古兴起以来,它更成为检验圣经历史可信度的关键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