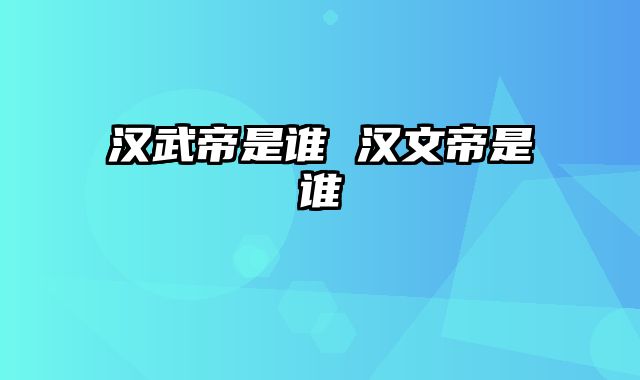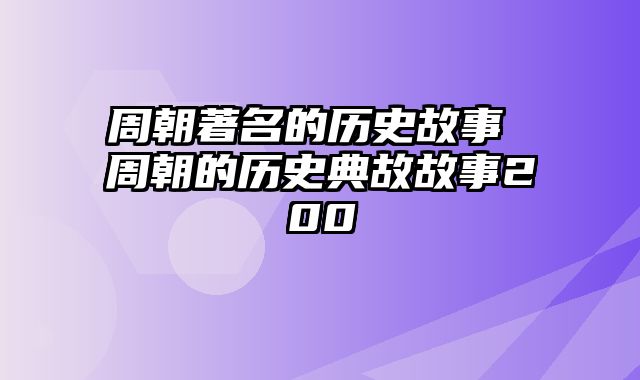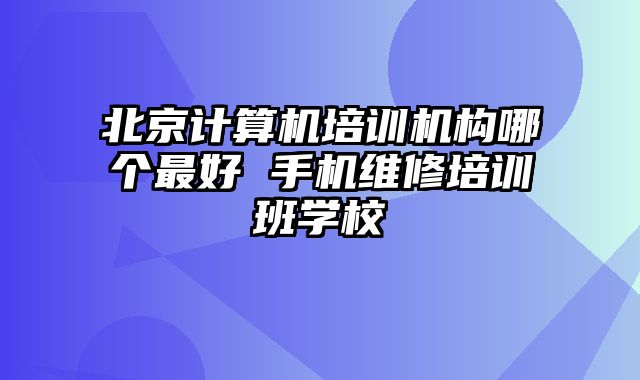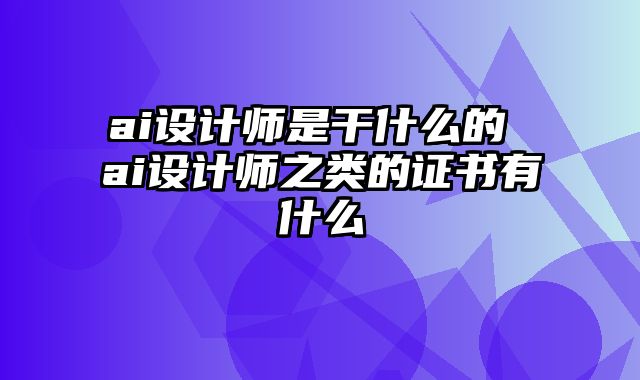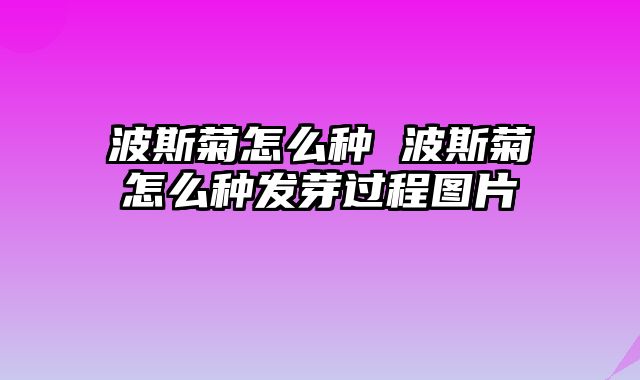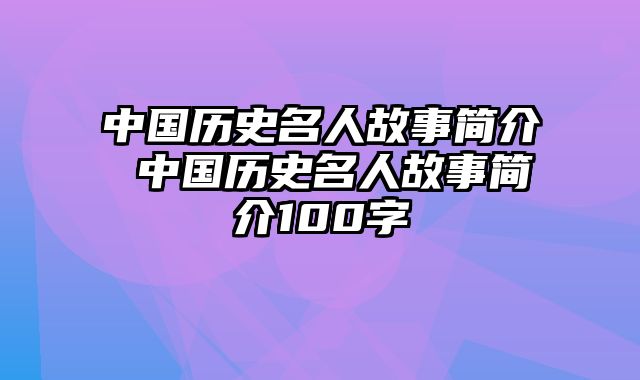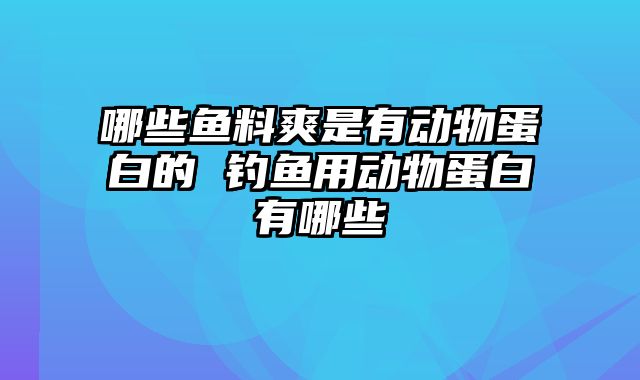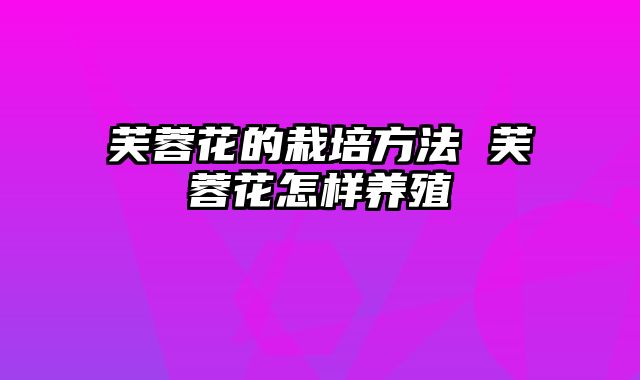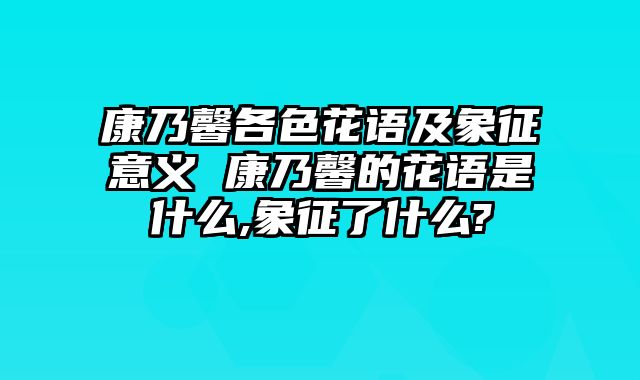历史背景方面,整理党务案的出台绝非偶然。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式开启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积极参与各级党部建设:至1926年初,全国23个省区中,有18个省的国民党省党部由共产党员实际主持;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县市级党部多由中共骨干领导;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农民部、宣传部等核心部门,亦由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中共党员担任要职。这种深度嵌入,既壮大了国民党基层组织,也使中共迅速获得政治历练与群众基础。但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以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为代表的右翼力量日益焦虑。他们视中共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群众动员能力突出为对国民党“正统性”与“领导权”的潜在威胁。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权力真空加剧派系博弈;同年“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公开反共;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以“肃清阴谋”为由软禁汪精卫、驱逐苏联顾问、解除中共掌握的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些均构成整理党务案的直接前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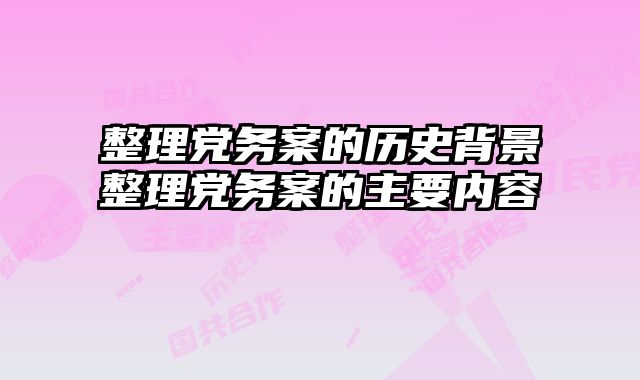
在此背景下,1926年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会议由蒋介石主导,提出《整理党务案》八条决议,经表决通过。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维度:一是组织限制,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已任职者须辞职;二是人事管控,要求“共产党员名单须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检查”,并“限制跨党党员在各级党部委员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三是制度隔离,明确“凡属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其他政治团体”,变相否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法理基础。此外,还规定“国民党各级党部执行委员中,共产党籍委员须退出”,并设立“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监督党务执行。值得注意的是,该提案虽由蒋介石授意、陈果夫等人起草,却由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中共代表谭平山、林伯渠等被迫签字认可——此举暴露了中共中央当时“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妥协路线:陈独秀主导下的中共领导层误判形势,认为退让可维系合作大局,甚至将提案通过视为“避免分裂的必要代价”。
整理党务案的后果极为深远。短期看,中共丧失了在国民党中央及多数地方党部的实际领导权:谭平山辞去组织部长,毛泽东辞去代理宣传部长,林伯渠卸任农民部长;全国范围内约200名中共党员被迫退出国民党党部职务。长期而言,它彻底改变了国共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基础:国民党右翼由此完成组织清洗与权力重组,为1927年“四一二”清党铺平道路;而中共则在组织上被边缘化,在舆论上被污名为“破坏统一”的异质力量。更关键的是,该案暴露出共产国际指导方针与中共本土实践之间的深刻张力——莫斯科强调“利用国民党发展自身”,却低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排他本能;中共强调“党内合作”,却未建立有效反制机制。历史证明,放弃独立领导权、放弃对武装和群众组织的实际掌控,仅靠组织让步无法换取政治安全。
值得反思的是,整理党务案并非孤立文本,而是多重历史逻辑交汇的结果:它是国民党内部权力再分配的工具,是蒋介石积累个人权威的关键跳板,也是大革命时期阶级矛盾激化的制度投射。从档案史料看,蒋介石在会前已密令黄埔军校及驻粤部队加强戒备;苏联顾问鲍罗廷虽反对该提案,却未能阻止;汪精卫因“中山舰事件”后暂离中枢,缺席会议,客观上使右翼提案得以顺利通过。这些细节揭示出,所谓“整理党务”,实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围猎。而中共的被动接受,也成为此后总结“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历史结论的重要反面教材。
今天重审整理党务案,不仅在于复原史实,更在于辨析合作政治中的权力本质:真正的统一战线,从来不是单方面让渡组织主权,而是在共同纲领下保持政治自主性与组织独立性。该案警示后人,任何忽视阶级属性差异、模糊斗争策略边界的妥协,终将付出沉重历史代价。它既是大革命由盛转衰的制度性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政治成熟不可或缺的历史课业。
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的《整理党务案》,是国共合作时期具有转折意义的政治事件。它表面以“统一党内纪律、厘清组织关系”为名,实则标志着国民党右翼势力系统性排挤共产党人、削弱中共在国民党内合法地位的关键一步。要深入理解这一事件,必须将其置于1924—1926年国共合作急剧演变的宏观历史脉络中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