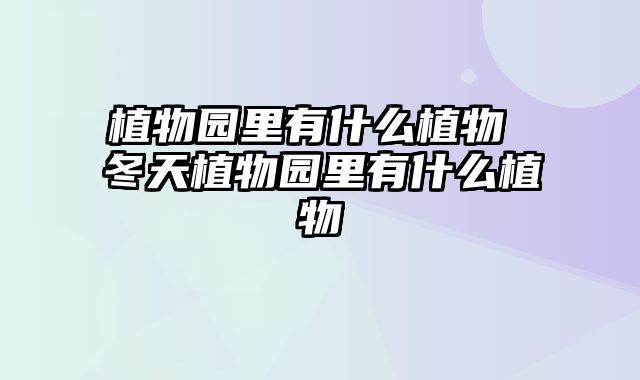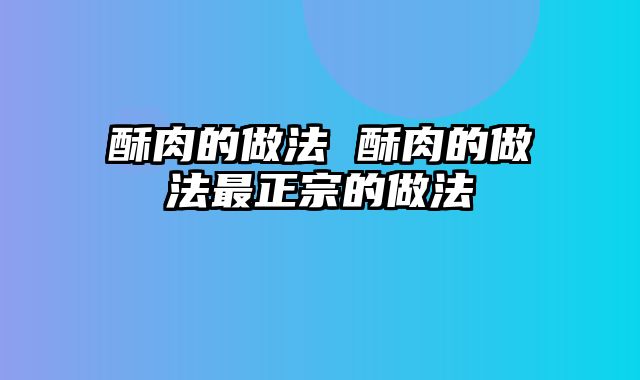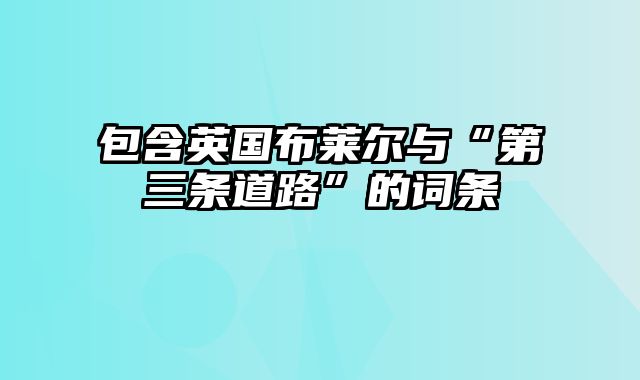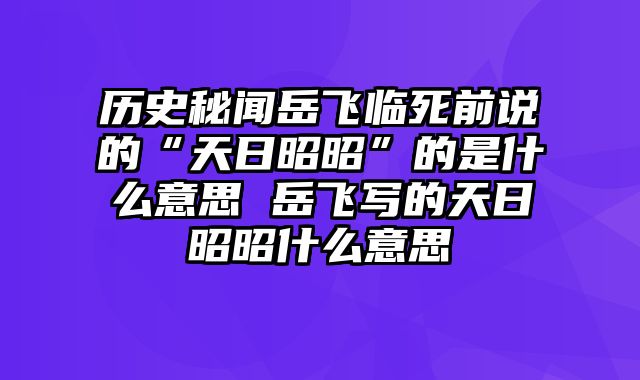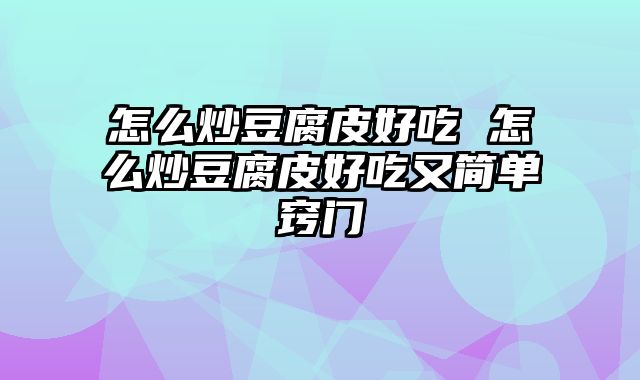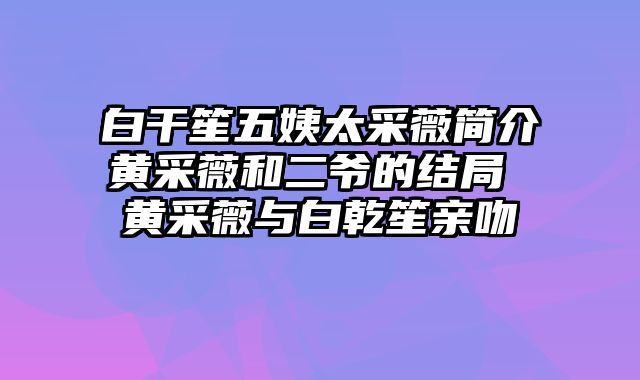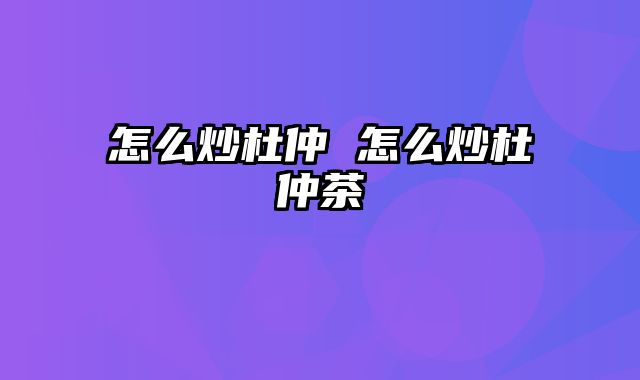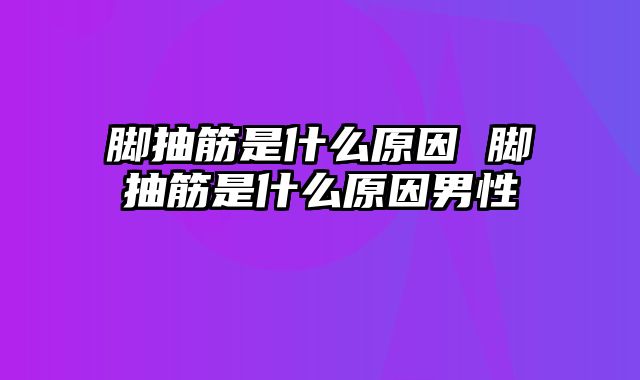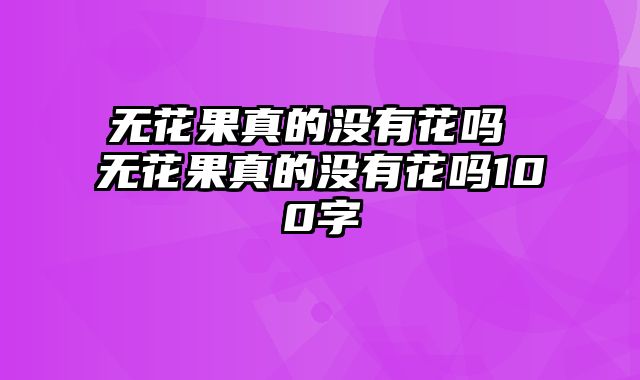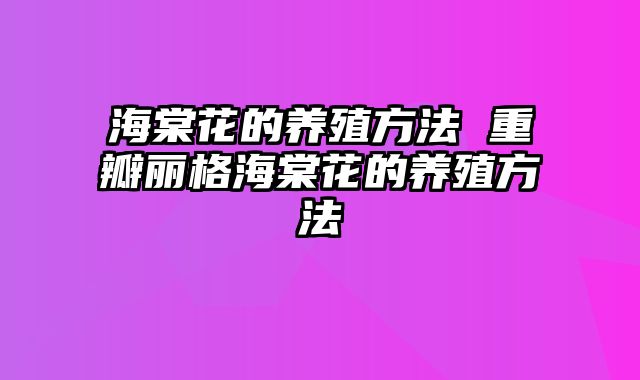屈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其作品不仅开创了楚辞体新范式,更以深沉的家国情怀、瑰丽的神话想象与峻洁的人格理想,构筑起中华诗歌精神的巍峨高峰。他的诗句穿越两千三百年风雨,至今仍激荡人心。要理解屈原的经典诗句,不能仅作字句摘录,而需置于战国末期楚国政治衰微、文化勃兴的历史语境中,结合其忠而见疏、信而被谤的人生轨迹,方能体会字字血泪、句句金石之重。

最广为传诵的当属《离骚》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此非寻常自述家世,而是以远古圣王高阳氏(颛顼)后裔自许,将个体生命锚定于华夏文明正统谱系之中,奠定全诗“美政理想—人格自守—上下求索”的精神主轴。紧随其后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首次在汉语诗歌中系统提出“内美”与“修能”并重的君子人格模型——内在德性如兰蕙芬芳,外在才能似秋菊凌霜,二者统一方为完人。这一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儒家“文质彬彬”的修养观。
《离骚》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堪称屈原精神最凝练的诗眼。它超越个人仕途失意,升华为人类面对真理、正义与理想时永恒的实践姿态。“上下”既指空间维度的叩天问地(如《离骚》后半段神游昆仑、驱使龙凤),亦喻时间维度的古今求索(追思禹汤、对比桀纣)。此句之所以历久弥新,在于它拒绝宿命论与虚无主义,以行动哲学赋予绝望以尊严,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的精神口令。
《九章·橘颂》则展现屈原另一重经典面向——以物明志的象征诗学。“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表面咏橘,实则立誓:“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橘树扎根故土、不随流俗的生物特性,被升华为楚人文化认同与士人政治气节的双重隐喻。这种“比德”传统(以自然物象比拟道德品格)经屈原淬炼,成为《诗经》“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转化,直接启导了陶渊明咏菊、周敦颐爱莲等后世咏物诗脉。
《渔父》中的对话体诗句同样具有典范意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并非孤傲宣言,而是价值坐标系崩塌时的清醒确认。当渔父劝其“与世推移”时,屈原答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岂能以洁净之身,承受尘世污浊?此处“察察”与“汶汶”的音义对举,形成触目惊心的道德张力,将洁身自好升华为存在论层面的抉择。这种以生命为代价捍卫精神纯粹性的决绝,在《怀沙》绝笔“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中达到顶峰——他选择以形骸之沉没,换取精神之永立。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诗句的经典性还体现在语言革命上。他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扈”“搴”“汩”)、神话意象(羲和、望舒、飞廉)、香草系统(江离、辟芷、秋兰、宿莽)及参差句式(“兮”字句的咏叹节奏),打破《诗经》四言桎梏,创造“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全新诗体。《湘君》“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的悖论式书写,以不可能动作凸显求而不得的焦灼;《山鬼》“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的情景互渗,则将自然律动与心理节奏熔铸为抒情合金。
这些诗句之所以跨越时代成为经典,根本在于其承载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命题:个体如何在权力结构中持守道义?理想幻灭后精神何以自处?文化根脉如何通过审美形式代代相续?王逸《楚辞章句》称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刘勰《文心雕龙》誉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从贾谊《吊屈原文》到李白“屈平词赋悬日月”,从苏轼“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到闻一多视其为“人民诗人”,屈原诗句早已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参与民族精神建构的活态基因。今天重读“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们触摸的不仅是战国士人的悲悯,更是贯穿中国历史的民本思想温度;吟诵“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激荡胸中的仍是每个时代坚守者共通的生命热力。屈原诗句的经典性,正在于它们既是特定时空的产物,又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