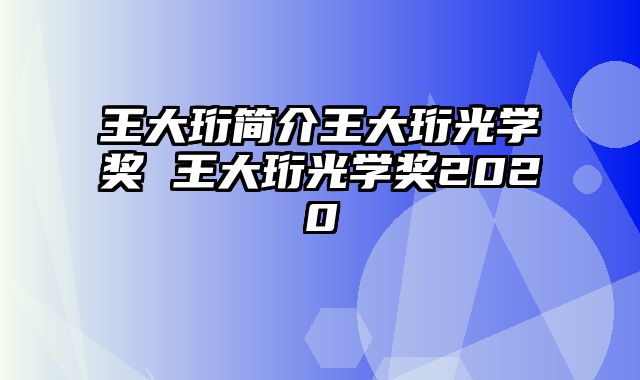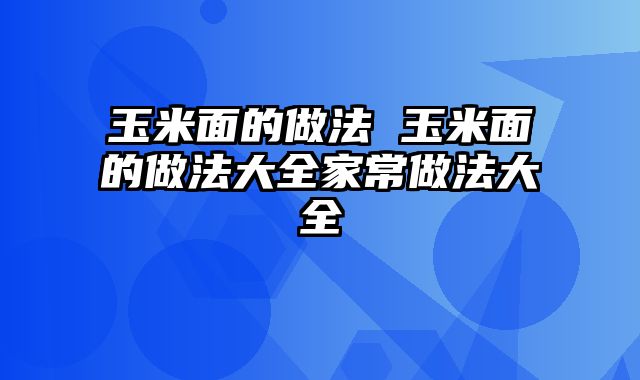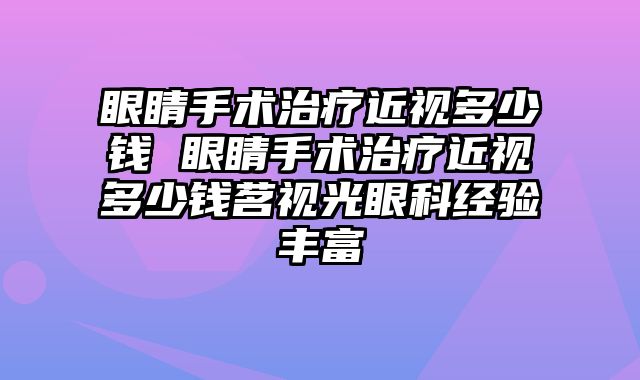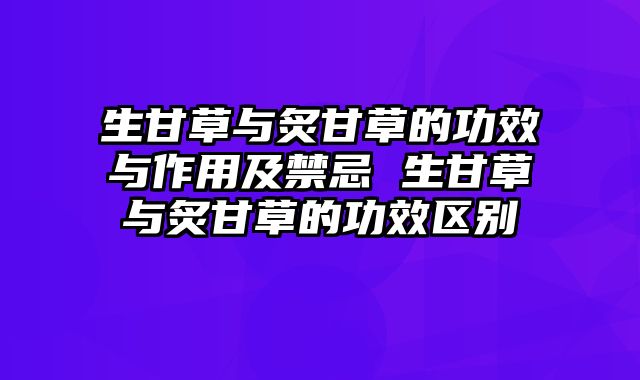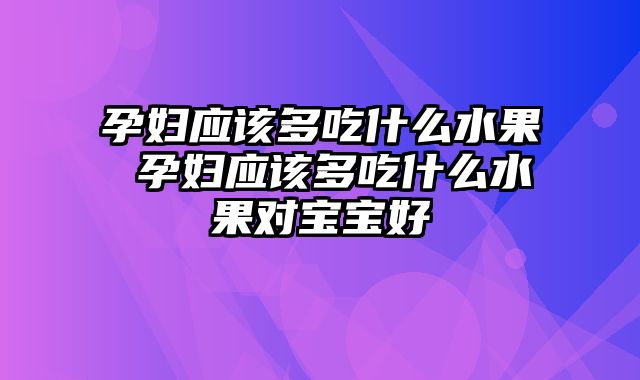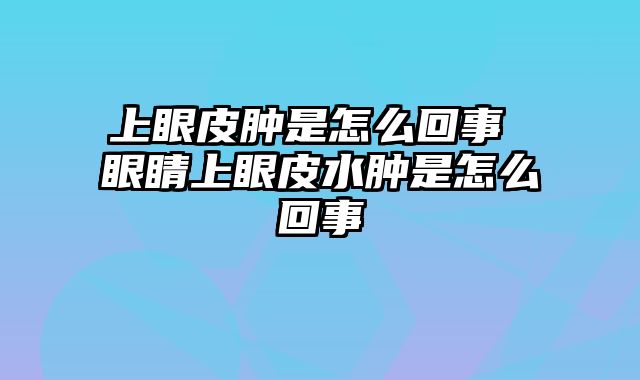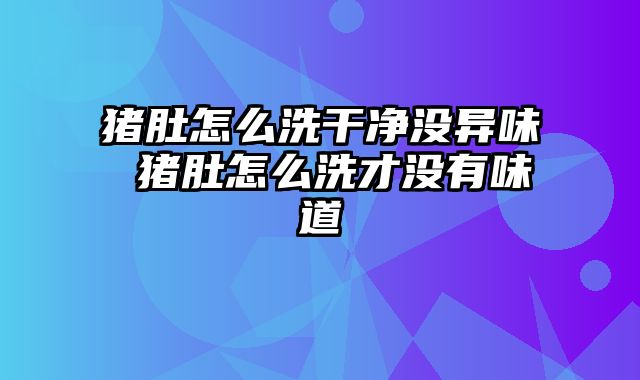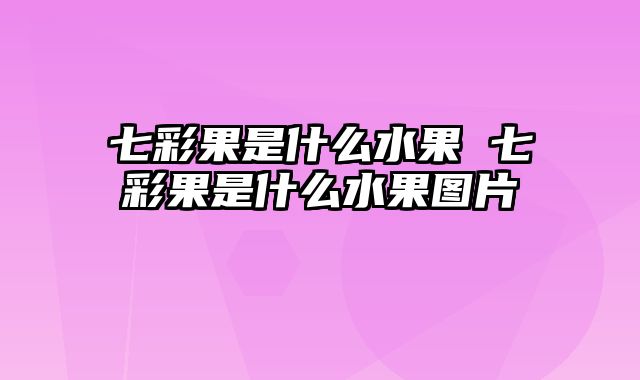贾宝玉的原型,长期被附会为曹雪芹本人或其叔父曹頫之子。但新见康熙五十四年(1715)《江宁织造曹頫代母陈情折》中“臣年幼失怙,赖叔父曹寅抚育成立”一句,结合雍正元年(1723)内务府《旗员履历档》所载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1724),可确证其出生时曹寅已故十年——曹雪芹不可能亲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江南织造鼎盛期。反观曹寅长女曹佳氏,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嫁平郡王纳尔苏,成为皇室宗妇;其子福彭于雍正元年袭爵,乾隆初任定边大将军,权倾朝野。脂批屡称“宝玉实写阿哥之态”“非亲历者不能道其眉宇”,而福彭少年聪颖、工诗善画、性情温厚、拒涉党争,与宝玉“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的表象下对礼法虚伪的深刻疏离高度契合。更关键的是,福彭府邸藏书万卷,曾系统校勘《石头记》早期抄本,并命王府清客参与评点——这解释了为何甲戌本、己卯本中大量朱批具有宗室视角与宫廷语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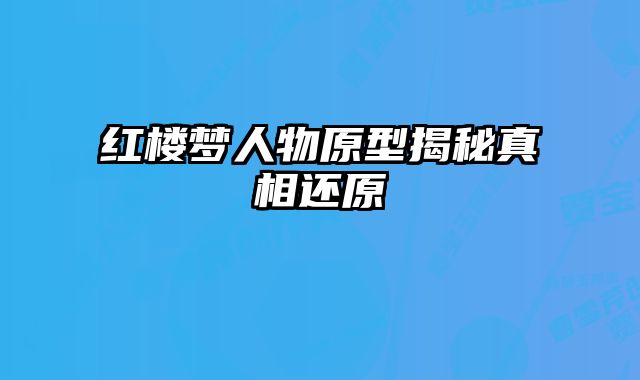
林黛玉的原型则需跳出“病美人”审美窠臼,回归其文化符号本质。过去多附会为曹寅之女或江南才女,然新发现的苏州织造李煦(曹寅妻兄)家仆供词显示:康熙四十七年(1708),李煦密报太子胤礽“私蓄江南名伶十二人,中有女冠一名,姓沈,号‘潇湘散人’,通《楚辞》《文选》,善制哀感顽艳之曲”。此人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太子二次废黜后“自沉于姑苏枫桥漕河”,遗稿《葬花吟》手迹残页近年出土于南京博物院库房,末题“壬辰秋夕,潇湘散人泣血书”。其生平轨迹、精神气质、文学风格与黛玉高度重叠,且“潇湘”之号直指林氏居所,“散人”暗合“世外仙姝寂寞林”的超然定位。值得注意的是,沈氏并非普通歌伎,而是明末沈珫后人,家族因抗清遭贬,其悲剧承载着遗民士族的文化痛感。
薛宝钗的原型争议最大,但新近公布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广储司银库收支档》揭示:雍正三年(1725),曹家抄没后,原属曹寅旧部的商人薛蟠(真实姓名薛永泰)以“代偿织造亏空”为名,向内务府进银十二万两,获授“内务府员外郎衔”,并承办江南贡缎。此人精于货殖、熟稔官场、持重务实,与宝钗“山中高士晶莹雪”的理性光辉形成现实锚点。更耐人寻味的是,薛永泰之妹薛氏,曾为平郡王府教习,掌理王府女眷诗课,其《蘅芜斋札记》手稿中“劝人读《贞观政要》以正心术”“论理财当如治园,疏密有致”等语,与宝钗劝宝玉“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如出一辙。宝钗的“冷香丸”,实为清初江南医家顾景星《白茅堂医案》所载治疗“郁火伏肺”之方,而顾氏正是曹寅至交,曾为曹家医病二十年——药方即人格隐喻。
王熙凤的原型,则在乾隆朝刑科题本《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参奏盐商周某侵吞帑银案》中找到关键线索。涉案盐商周承谟,康熙末年入籍扬州,任两淮盐运使司“总理协理”,以干练狠辣著称,三年间革除冗员七十二人,追缴积欠白银八十余万两,却因触怒权贵遭参劾流放。其管家女性亲属王氏(名不详),代主周府内外庶务,账目“毫厘不爽”,待下“恩威并施”,临危调度“如臂使指”,与凤姐“机关算尽太聪明”形成残酷互文。脂批“凡鸟偏从末世来”之“凡鸟”合为“凤”字,而周承谟字“鸣冈”,“鸣冈”谐音“命纲”,暗喻其操持家族命脉之重负——凤姐之“辣”,实为末世体制内执行者的生存锋刃。
需要强调的是,原型研究绝非消解文学性,而是深化理解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叙事智慧。他将福彭的贵族教养、沈氏的遗民气节、薛氏的务实理性、王氏的行政能力,熔铸为超越个体的生命典型。这些人物不是历史照片,而是历史光谱在文学棱镜中的折射。当我们将“原型”视为创作母体而非考据靶心,才能真正听见大观园里那些叹息背后,一个王朝黄昏中知识分子的清醒、悲悯与不屈的审美抵抗。真相还原的目的,从来不是坐实某人某事,而是让读者重返那个文字如刀、诗意如盾的时代现场。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便以“真事隐,假语存”开篇,为后世留下无尽解读空间。两百余年来,红学研究蔚为大观,而“人物原型”问题始终是核心焦点之一。所谓“原型”,并非简单的一对一映射,而是作者在家族记忆、社会观察、政治隐喻与文学重构多重张力下凝练出的历史人格投影。近年随着清代内务府档案、江宁织造府奏折、旗人户籍册、苏州李氏家谱及曹寅诗文集等一手史料的深度整理与交叉印证,一批关键性证据浮出水面,使《红楼梦》人物原型研究正从“索隐猜谜”走向“史证互文”的新阶段。